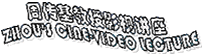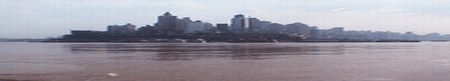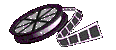我们提出的争论焦点,即对任何影片画面中的全部因素的感知都是不偏不倚的,这明显与十九世纪艺术评论家所眷恋不舍的,后来又为二十世纪的一些摄影家所全盘接受的那种思想背道而驰的,他们相信,人眼是根据固定的路线来探索画框中的画面的,人眼首先聚焦在所谓的“构图焦点中心”(一般取决于久经推崇的“黄金分割律”),然后沿着一条据说是取决于主导线条的配置路线来通过那个构图。爱森斯坦本人也相当热衷于这一思想,他对《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冰湖大战序幕视觉部分的分析就是以此假说为基础的。这一概念在今天的美术评论中已经过时,正如以黄金分害乃律为依据的构图在绘画艺术中也已过时了。即使十九世纪的眼晴确实是以这种方式来看事物的,现代的眼睛却并非如此。
任何电影画面显然包括一些因素较其它因素更强烈地引人注目,例如一个在说话的人一般是首先被注意的对象。这确实如此,但是我们依然意识到构图的整体,其中说话的人只是一部分,而且我们特别意识到那个实际的四方形画框,哪怕画面的背景是全黑,或白,或灰的。因为“注视”涉及到思维过程,而反过来,“看”则涉及到眼睛的生理学。当我们观看一部影片时,正如我们在观看一张照片或一幅绘画时一样,看不再取决于“注视”,而在实际生活情境中,几乎始终是“看”取决于“注视”;这种涉及注视的选择性丝毫不再影响涉及看的无选择性。
但是,这一切问题都有一个重要的条件:观众必须坐在距离银幕合适的位置上。如果他坐得太近,近到连他的视野都不能把银幕包括进去,那么当视觉兴趣中心移动时,他的眼睛就必须改变焦点,而且他始终无法掌握那个画框中的画面所创造的整体视觉效果。另一方面,如果他坐得太远,画面都变得如此简略,他只能看到那些兴趣的中心,面他所看到的那个画框要比电影创作者在拍掇这个镜头时通过取景器所看到的还要小(取景器的画框,我们应当记住,容纳了人眼的全部视野),因此作为构图基础的最初原则就会遭到破坏(正如在绘画中那样,一种特殊的构图不是在任何大小的画框中都能获得成效的,每一种构图似乎都有最适合于它的尺寸)。考虑到这些以及其它问题,人们从数学上确定,最佳的观看距离大致是银幕宽度的两倍。在目前情况下不太可能使剧院的每一个观众都能和银幕保持那准确的距离(哪怕是在合理范围的位置上),这一事实并没有使这一原则无效,但是却明显地表明,将来建筑的影院必须是不同的。
一旦电影创作者认识到这里所概括的电影画面的性质,那么他会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最明显的,画框必须始终作为一个整体构图来加以构思,然而,构成任何一个镜头的可能方式就象每个电影创作者的气质那样的千变万化,而一般的构图问题则超越了本书范围。另一方面,很少有电影制作者意识到,更不必说关心,镜头转换的组织可能性,也就是说把镜头之间的表达看作是每一个接下去的镜头的整体构图的功能,从而创造一种能够把本书以上所论述的以及后面的章节所论述的形式因素结合起来的结构框架。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义务,如果他们对于有机地处理电影制作的素材的迫切需要还敏感的话,他们本应意识到。
静态的表述
一般来说,第一个电影制作者致力于把抽象的电影形式在“比喻性的”电影创作中具体体现出来的就是谢尔盖"爱森斯坦。他也是实际把自己对形式的探讨著书立论的很少几名电影创作者之一。
爱森斯坦对他的第一部杰作《战舰波将金号》的分析强调影片的总体结构,他指出该片的结构是以古典悲剧的五幕剧的格局,以诗的韵脚,首先是以黄金分割律为基础的;然后,以影片中那著名的敖德萨阶梯段落为实例,他讨论了通过剪辑来实现的造型组织。
爱森斯坦告诉我们,这一段落的剪辑是以不同镜头的富于动态( 俄文应为“动力学”)的内容之间的对立为基础的( 例如快速的动作与缓慢的动作相对,向上的运动与向下的运动相对),以及以镜头景别之间的对立为基础的(因此还有每个镜头内人或物的数量的多寡之间的对立)。在这段具有历史意义的段落中那总合的不寻常的美学张力是通过这些形式对比的相互作用创造出来的。
当他分析《总路线》中宗教出游的时候,爱森斯坦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他称之为“多声部蒙太奇”,一个段落中不同“人声”的一种音乐性的交织(热情、狂热,唱歌的人的镜头,唱歌的妇女的镜头);这还包括镜头景别的变化。
爱森斯坦的伟大发现之一(但他似乎仅仅是信笔写到的)就是他把剪辑看作是海一个接下去的镜头的构图功能,尤其是在涉及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同一个被摄体的一系列镜头的情况时。
要理解这是从哪里继承来的,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在爱森斯坦把他的艺术兴趣从绘画转向戏剧和电影以前几年的时候所诞生的一个绘画流派。我当然指的是立体主义,尤其立体主义实验的那个方面。最典型的或许就是在1912年左右由璜"格里斯对乐器所进行的各种研究(虽然意大利未来派实例在这里也合适)。如果研究一下象《小提琴与六弦琴》(1913)这样的绘画,我们就会发现,可以看作为主导动机的是那个由三个紧紧“框起来的”指板的再现所组成的,还有在它们之间的是音板的一个“特写”。如果把这幅画简化为对一个物体的这种的视角,以至发展到认为这就是它的主题,这可能是过分简单化了,但是它却可以看作是对于爱森斯坦在十年左右以后发展的那种有关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同一被摄体的镜头剪接进来的美学策略的一种预兆性说明。现在可以认定,格里斯的绘画所提供的部分乐趣并不是仅仅来自同时看见从若干角度来加以描绘的被摄体,而是来自眼睛的这样一种过模,即把每一面加以比较,去辨别它们在新的伪装下的“客观”共同特征,把差异和类同相比较,一句话,在不连贯中发现连贯性和反之。现在,根据眼睛对形状的记忆方式,从不同角度拍摄同一被摄体的两个镜头,可以获得和镜头交又剪辑起来时同样的审美满足。更为特殊的是,两个镜头转换时轮廓与区域的变化,相对于画框边线所提供的固定坐标----能高度满足眼睛的张力和排列组合的作用,由于这些变化的复杂性和统一性,它们是能够加以构成的。
这里很明显有一个结构的潜力,尽管我们必须承认,上述满足的性质是相当模糊的。但是这种快感确实有相应的比较具体的因素为根掘,似乎由所谓30度规律的存在所肯定了。这是在二十年代从经验中确立的,“已规定对同一摄影主体的新角度必须和前一角度和30度的差别。电影创作者注意到,任何少于30度的角度变化(因此,不考虑改变角度的摄影机的前后移动——英国人称为“拉手风琴”)就造成一个“跳跃”,这就会使观众模模糊糊地感到不舒服。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无疑是由于这种切换的太小,不容易分辨的性质;新镜头和前一个镜头没有显著的差别,特别是当两个镜头是从相近似的摄影机与被摄体的距离拍摄时。但是人们也可以说,这种不舒服是由于这类切换根本没有视觉目的,观众之所以感到一种模糊的不安,主要是来自他的眼睛受骗这一事实,因为眼睛要求,如果他所看见的形状要有什么变化的话,这种改变必须是引人注目的,以及它所获得的张力应当是明确和显著的。
我们可以扼要指出,虽然这条规则教给我们有关镜头变化性质十分重要的东西,但是它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少于30度的角度变化早已成为现代电影创作者的语汇的一部分了,因为我们已在讨论常人视线的匹配和银幕方向的匹配时指明,小毛病和不舒服可以是提供创造张力的十分有用的因素,正如戈达尔的《精疲力尽》和塞缀尔"富勒的许多影片所表明的,其中有大量的跳切,而一般都是出现在极端暴烈的时刻。
我们说过,爱森斯坦大概是第一位电影创作者把画面构图看作是影片的每个画面之间的全面关系的功能。在《十月》里,教堂塔的一系列仰角度镜头是由简单的相反对角线组成的,而悬挂的自行车的段落则使用了一组简单而又迷人的在黑色背景上的闪闪发光的各种圆形。《总路线》包含一系列牛奶分离器喷嘴的极快的闪现,创造了种种空间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有些更为复杂,它牵涉到从或多或少明显缩短的喷嘴和“未经歪曲的”正侧面的同一喷嘴之间的对比。同样有效而更基本的是,一列大车由一台巨大无比的拖拉机拖过田野的众多的相反方向的空间关系。但是,这一空间重新拘阎方法的最完善的实例可以在爱森斯坦那部被压制的影片《白静草原》的开场段落中找到。这一段落围绕着一个躺在大车上的妇女尸体,她的儿子在哭泣,父亲则站在一旁。这幅“画“中的每个因素都在接下去的一个个镜头中出现,然而每次重现都彻底做了重新安排,从而造成在最初的那个空间中形成全新的变化。不幸的是,我们已不可能详尽地分析这一段落,因为这部影片仅以放大的画面剧照的形式传了下来,这就是它所遗留下来的一切。然而我们依然足以把它看作是爱森斯坦在这一特殊方面的成熟的成就。另一方面,《伊凡雷帝》却包含看另一种有意思的对比。在贵族们在等待那预期的伊凡死讯的那场戏中,开始是三个表现几组焦急面孔的密集镜头。每个镜头的背景都是同一个照得通亮的圣像,只不过每次都处于画框中的不同位置。在人形上的构图是相似的,而圣像的构图则是不同的。十分清楚,在这些镜头之间是无法匹配的(人形与圣像的相关位置显然做了篡改,从而在镜头转换中获得令人满意的重新组合)。这种篡改破坏了空间“连贯性”那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则之一,并且总他说来,其结果是产生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种失去方位和稍感不适的感觉。但是这里却完全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爱森斯坦在这里设法创遣了一个极不寻常的电影空间:它只存在于这个段落中的镜头的总合体之中;我们不再有那种赋予了独立存在的环境空间感,而一系列镜头似乎是从其中萃取出来的。相反的,我们看见了一个以布拉克的台球台那样多面而复杂的方式存在着的空间;我们看见的一个场景是体现在一系列镜头中各种透视的总合,这一场景的内聚力是由各个镜头的和谐的表述所创造的。这显然是罕见和困难的成就。在伊凡的“死亡室”中出于类似的构图原因所采用的若干同样不匹配的镜头(其原因主要是为照顾每个单独镜头内的绘画性的和谐),只不过造成一种“出了毛病”的感觉。这个房间的空间统一在出现这孤立的几个不匹配的镜头的前后已经交代得过于明确了,因此我们只能感到那几个镜头无缘无故地破坏了那个和谐。但是前面论述的贵族们的那几个镜头的用法是对头的,它们暗示出,镜头空间该怎样首尾一贯地来加以表达,从而使那个空间是“开放”的,并且证明,从镜头到镜头的转换时,被掇体的排列设计得越仔细,那么这种“开放性”就越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