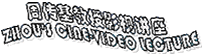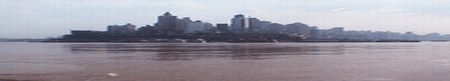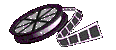|
(我在上海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的一场争论,在这世纪之 末发人深思。这场争论内容分做两次发表)
亦谈电影票价
周传基
最近《泰坦尼克号》在国内公映时的惊人票价与观众的踊跃购票的情况
似乎是引起了电影界人士的关注。有人惊呼这是一种不合理的“高消费”,有人分析“物美”与“价廉”的消费心理,有人还高喊要对好莱坞的
挑战加以应战。但是就是没人把为什么《泰坦尼克号》卖得天价的票和
国产片连本儿都收不回来的情况的内在原因谈清楚。
其实所谓的“高消费”是观众自愿的,那怕是占一般职工(下岗人员不
计算在内)月薪的百分之二、三十,谁愿意买,谁买。你管不着每个人
消费分配。你可知道“外满中空”之说?前几年有些重点国产片是由工
会集体买票白送给职工去看的,由于是包场,所以票房门口挂出“客满”的牌子,可是开映时,电影院放映厅内的观众却寥寥无几。那叫白送都
不看。工会却因此倾家荡产,把收来的会费全都买了电影票(因此现在
也没法照顾下岗会员了)。难道那些电影界的人士不知道这些观众买高
价票时是一种透支心理?观众如果喜欢看某部影片,因此把看十部影片
的票钱集中优势兵力,一次花了。也值。因为估计后来的九部也不值得
一看。而对于发行商来说,他们才不管什么民族电影事业存亡不存亡的
问题。这种高票价的运作从长期来看,虽然对他们来说也是饮鸩止渴,
但从短期行为来说,这叫不捞白不捞。这部片子挣足了,还可以补贴后
面那些不卖座的影片的亏损。否则是两头空。
所谓的“物美”论又是一种故做深奥的时髦论调。要知道,看电影不是
生活的必需,好看就看,不好看就不看。看得起就掏钱,看不起就不掏
钱。观众的神经十分健全。观众喜欢“物美价廉”的影片,但是现在的
事实不是“物美价不廉”,而是“价廉物不美”,所以掏得起钱的观众
宁肯选择“物美价不廉”的影片来看了。不知“物美”论者自己是怎样
对待这个问题的。可以想象得到。正如某企业厂长在大谈广告美学时,
自夸他对本厂生产的电视机的宣传如何高明,但是当有人问他家里摆的
是什么电视机时,他支吾地说:松下。
至于说到准备对好莱坞电影儿挑战的应战,我不禁要问,拿什么来应战?文学性?后期配音?!直到现在,还有的“电影评论家”或“电影理论
家”在那里大加赞扬后期配音的膺品,还承认它们是作品,并且煞有介
事地深入分析它的什么两个时空,三个时空等等,其实连一个时空都没
有。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有人号召中国电影创作者们要拿出自己的志气
来与好莱坞霸权决一雌雄。可我看首先需要的不是志气,而勇气,坚决
否掉“电影综合艺术论”的勇气,然后志气才能有用武之地。可是我们
现在有很多电影工作者连电影的纪录本性都没有弄清楚。瞎糊弄观众。
比如说,在我们的大小银幕上,抗战前的土匪使用的是八十年代制造的
先进武器、1938年以前的国民党空军竟有美国的飞机与武器,等等。这
种片子拍出来竟然还得政府奖,也就是说得到官方的鼓励。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有能力搞出与好莱坞电影儿相抗衡的产品来吗?先别奢谈什么
文化内函,当我们尚未搞清什么是电影的本体之前,还是老老实实地从
头学起吧! 不要把头钻在沙子里,让我们来看一些事实。据《中国电影市场》杂志
的报导,全国十城市98年4月新片票房排行情况如下:
在京,《泰坦尼克号》的平均票价为40.8元人民币,观众人次为619,118 ,收入为两千五百万人民币,而《爱情麻辣烫》的平均票价为10.59,观 众为197,949人次,收入为两百万人民币。《泰坦尼克号》在上海的平均 票价为28.7 元人民币,观众人次九十八万,收入为两千八百多万。如果 仅从文字报导来看,《海之魂》在上海的票房相当成功,可是看看不饶 人的具体统计数字,它的平均票价为5.8 人民币,观众人次仅八万余, 是《泰坦尼克号》观众人次的零头,票房收入为四十八万二千余。《泰 坦尼克号》在广州的平均票价为41.3元人民币,《周恩来外交风云》的 平均票价为4.5元人民币。在哈尔滨,《泰坦尼克号》的平均票价为39.9 元人民币,在长沙为23.3元人民币,在重庆为19.6元人民币,在太原为 14.2 元人民币。观众人次均在六位数字以上,收入均超过百万。其它影 片的收入没有超过百万的(深圳特区的数字出现很大差错,故不计在内 )。不仅如此,而且还有不少观众居然声称从《泰坦尼克号》那好莱坞 的陈俗滥套中获得教益!这时可把那至今没有申明有所改变的“意识形 态不能让步”的原则给忘了,居然公开宣称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那里获 得教益。 其实《泰坦尼克号》占领中国电影市场的事件并非第一遭。记得在八十 年代末,好莱坞电影儿《霹雳舞》(BREAK_DANCE)在某年年底也曾 帮助我国的发行公司完成了当年的任务。我在当时就感到中国电影业的 情况十分不妙。有机会的话,我愿意和读者讨论一下,自七十年代末以 来,富有“拓疆精神”的好莱坞电影工业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入侵中国, 最后终于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其中包括起推波助澜作用的我国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和电影界的许多人士对金像奖的义务吹捧。 为什么《泰坦尼克号》这样一部外国的纯娱乐片会在中国获得如此惊人 的效果呢?它在上映期内甚嚣尘上,以至成为人人必看的社会事件。是 因为好莱坞对“电影综合艺术论”研究有方?文学性搞得好? 该是我们电影界深刻反省的时候了。某些问题不在我讨论的范围内,不 便涉及,但是有一个问题,而且不是一个小问题,是值得一提的。如果 我们都能诚实地对待现实的话,那事实就是电影诞生一百多年了,而我 们还没有真正学会拍电影。因为我们至今还在电影里研究其它艺术。这 是一颗非吞不可的苦药丸。 有人会认为这个周某不知天高地厚,口出狂言。是吗?随便拿此时此刻 电影频道上放映的国产影片《双栖间谍》来看。在银幕上,当国共两党 在讨论合作抗日的过程中,发生磨擦,矛盾,甚至动起武来,中国人打 中国人,双方都使用了先进的半自动步枪。可是我知道在抗日战争中国 共两党的军队都没有拿出他们所拥有的那些先进武器来对付外来的侵略 者日本鬼子,而用的是汉阳兵工厂造的老式步枪。为什么?这可要问导 演啦。还有,美国军用吉普车是1942年才设计出来的,那么在影片故事 发生的那个时代,那些吉普车是谁造的。为什么国民党的军队会戴小日 本的钢盔。另外,三十年代是不跳圆舞曲的。导演怎么搞的。乱来。而 且何止是这一部影片。多啦。我看就差没有给秦始皇派一辆小轿车了。 这种影片没有观众看是很自然的。可是综合论不考虑这些。他们考虑如 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我们还没有学会拍电影? --与周传基先生商榷 郑雪来 周传基同志在今年8 月29日一期《文汇电影时报》发表的《也谈电影票 价》一文中,给“价廉物不美”的中国电影开出的药方,是要注重电影 的“纪录本性”,据他看,“重迭美学没有真正学会拍电影”,原因是 “我们至今还在电影里研究其它艺术。”这就牵涉到一系列电影理论问
题了。
不过,我们暂且撇下理论问题,先谈他所提的某些国产片违反纪录本性 的两个例子,即后期录音和与时代不符的问题。我想,在艺术上有所从 追求的电影导演,是打从心眼里搞同期录音的。为什么在我国电影界这 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说到底,是资金问题。记得张艺谋的《秋菊打 官司》参加金鸡奖时,大多数评委对该片的整体艺术质量都给以肯定, 尤其是对它同期录音所的真实性效果大加赞赏,但也些评委认为此片由 于是获得境外大量资助的合作片,其优越的资金条件所带来的技术效果 为纯粹国产片所不能比拟,无法在同一水平线上进行评比,所以,后来 金鸡奖就对合作片另列奖项,不与纯粹国产片混同。暂时不能搞同期录 音的原因,除了资金条件外,跟我们演员水平普遍不高也有关系。不少 演员连普通话都讲不好,还得另找人给他配音,你怎么搞同期录音呢? 道具等等细节的真实性当然是十分必要的,抗战前的土匪使用80年代制 造的武器,1938年以前国民党空军使用美国的飞机和武器,当然不行, 导演和道具员应该尽一切可能找到与时代相符的道具,找不到的话也要 复制,力求达到逼真效果。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议的,但同时我又觉得不 必小题大作,把国产影片不景气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一些录音、道具问题,甚至将其提到违反“纪录本性”的高度,恐怕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周传基同志所极力反对的好莱坞电影儿电影 倒是相当注重“纪录本性”的。他们绝对注意细节的真实性,为达到逼 真效果,可以把一连串豪华轿车毁掉,可以把一大批真的飞机烧掉。《 泰坦尼克号》在拍摄前就建造了一艘与原船长度和高度相仿的轮船,使 其在沉没时具有极度的逼真感。好莱坞电影儿其雄厚的拍摄资金和优越 的科技条件,毫无例外地彩同期录音。那么,它是否就符合了周传基同 志心目中的“纪录本性”呢? 周传基同志所说的“纪录本性”论,其实我们一点也不陌生,那就是安 德烈. 巴赞在《摄影影像本体论》中所说的“技术应保持所描绘的自然 物的暧昧性和多义性”。关于巴赞的电影美学观点,我国电影理论界曾 经历了近十年的热烈争论,我实在再不想说什么了。我只想提一点:我 国电影界其实对巴赞的论点也不是那么盲目推崇的,因而在80年代下半 期陆续出现文章指出“中国的巴赞热在理论上的错位”,“这种理论移 植中的偏颇”,“中国错误地再塑巴赞”,“一次历史性的误读”等等。 谁都不否认,电影具有纪录现实的功能。但是,电影是否就只纪录现实,而不解释现实,这就是“纪录本性论”和“形象本性论”争论的焦点。 按照巴赞的观点,现实是毋须解释的,艺术家的“介入”就会歪曲现实。实际上,世界上哪有艺术家不“介入”的艺术作品呢?深受巴赞理论影 响的法国新浪潮导演们不是也在“解释”法国现实吗?电影如果只有 “影像”(声音),而不塑造形象,这电影有人看吗? 周传基斥责我们电影界“还没有真正学会拍电影”,我看未免太主观了。我对我国电影的现状也不大满意。然而我国电影毕竟已经有了90多年的 历史,各个时期都出现过一些引起国际电影界瞩目的影片,你说这些都 不是电影,那又是什么?再说,电影学院近十多年来培养了那么多人才,而你说“还没有真正学会拍电影”,那你岂不是在否定自己的教学成果 吗? 实际情况当然并非如此。就拿最近在影代会上看到的电影学院毕业生李 少红执导的《红西服》来说,我看这就是一部“真正”的电影。影片通 过轻喜剧的形式表现下岗工人的遭际,即不回避当前尖锐的社会问题, 艺术处理上又很妥贴,毫无说教的意味。我看导演是很懂得电影的“本 体”的,看来她也并没有拘泥于所谓“纪录本性”,而象“生活流”般 去“纪录现实”,它倒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当前社会现实的本质的。 至于说到《泰》片是不是“‘电影艺术综合论’研究有方?文学性搞得 好?”且不去说它。我只想说,电影艺术综合性是客观存在,不必加以 反对。戏剧性冲突是当代电影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60年代在欧洲电影 界风靡一时的“非戏剧化”、“非情节化”早已成为历史陈迹。那么, 文学性呢?记得80年代初,我曾和张骏祥同志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我当 时反对的是他所提出的“电影就是文学”的论点,认为把电影归结为“ 文学”是说不通的,但我并不反对“文学性”。电影从文学是借鉴了许 多东西,各国许多作家都参加了电影创作,无数影片都是根据文学作品 改编的,怎么会不带有文学性呢?问题在于电影中如何采用。比如说, 抒情喜剧、讽刺喜剧、悲剧、史诗等等原本都是文学的概念,但电影完 全可以借鉴过来形成自己的特有样式。当今包括好莱坞电影儿电影在内 的各国电影都有一种“样式混杂”的趋势,即特定样式的标志已不那么 明显,这说明电影中对“文学性”、“综合性”的运用较前又有所发展 和变化,其目的都是为了达到更大的艺术效果。至于是否能达到,那就 得看创作者的本事了。电影正是要从其它艺术中继续吸取和借鉴一些东 西,“为我所用”,以增强自己的丰富性,如果仍旧像半个多世纪以前 先锋派那样强调“纯而又纯”,或者像二三十年前法国导演玛格丽特.
杜拉那样只认可所谓“纯音画”,那么今天的电影恐怕就只留下“影像”(再加上“声音”)而走向毁灭了.. 对好莱坞,我主张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既不要像某些人那样把好 莱坞电影儿奉若神明,就差点没有喊出“好莱坞万岁”的口号;但也不 必嗤之以鼻,而要进行具体分析。过去的好莱坞电影儿既有大量“梦幻 工厂”的制造品,又有像《居里夫人》、《一曲难忘》那样迄今值得人 们回味的作品,更不用说诸多《怒火之花》、《公民凯恩》之类批判现 实主义杰作了。当今的好莱坞诚然仍是“纯娱乐片“占主流,但毕竟还 是出现了不少比较真实地反映美国社会现实、抨击美国社会政治弊端的 影片,例如《现代启示录》、《生逢7 月4 日》等越战片,《沉默的羔
羊》、《阿甘正传》等社会片,更不用说深受全世界有正义感的观众赞 许的反法西斯影片《辛德勒名单》了。进行具体分析和认真研究,这也 许要比空喊“与好莱坞霸权一决雄雌“的口号或号召人们拿出“坚决否 掉‘综合艺术论’的勇气”,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更有一些好处。 什么叫“纯粹国产片” --兼与郑雪来先生商榷 舒 克 读《文汇电影时报》9月26日郑雪来的文章,得到一个信息:就是所谓“ 纯粹国产片“理论。郑先生透露,当年金鸡奖评选时曾对张艺谋的《秋 菊打官司》有过争议。“大多数评委对该片的整体艺术质量都给以肯定,尤其是对它同期录音所的真实性效果大加赞赏,但也些评委认为此片由 于是获得境外大量资助的合作片,其优越的资金条件所带来的技术效果 为纯粹国产片所不能比拟,无法在同一水平线上进行评比,所以,后来 金鸡奖就对合作片另列奖项,不与纯粹国产片混同…”原来,著名的金 鸡奖评选之所以另设合作片奖,是要将最佳大奖的位置腾让出来给“纯 粹国产片”。那么,什么是“纯粹国产片“呢?郑文中又有透露:就是 那些资金条件差的、“演员连普通话都讲不好”的、细节虚假到“抗战 前的土匪使用八十年代制造的武器“的这一类作品。在郑先生看来,对 于纯粹国产片在这些方面是不必“小题大作”的,否则就“拣了芝麻丢 了西瓜“。因为只有好莱坞电影儿才注重电影的“纪录本性”,才“绝 对注意细节的真实性”,而好莱坞追求的东西,我们自然也就不在乎了。 郑雪来先生无意间的揭秘,让人匪夷所思。长期以来,我们的金鸡奖一 直在鼓励什么?拒绝什么?为什么要用这“纯粹”二安人为地区分国产 片和我们的艺术家?不错,今天的张艺谋、陈凯歌拍电影确实不愁钱, 他们现在已拥有“境外大量资助”,确实与一般国产片不在“同一水平 线上”。倡,我们怎么能够忘记,张艺谋、陈凯歌们当初刚出道时,是 在怎样的艰难困苦中拼搏的。他们那时候的拍片条件(包括资金、资历 等各方面)恐怕远远低于同行们的同一水平线。然而他们的作品却能够 以高艺术质量明显越过了同行们的艺术水平线。他们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红高梁》等作品,无一不是在低资金、少援助的境遇下 拼搏出来的。他们用自己的艺术成就和实力赢得了外援,而当初比他们 条件优越得多的同行们,至今有几个能拿出相当的作品可与其并驾齐驱
的呢?记得1988年张艺谋应邀到南京参加《红高梁》首映式的时候,对 观众们说,他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更多的资金把那个“风舞高梁地”的镜 头拍得更美一些,“如若能有多机位拍摄,那组镜头肯定不一样”。因 此,他当时最希望得到的,就是能够用多机位拍摄的方式来完成他以后 的作品。张艺谋无非是想使自己的作品更加真实、更加完美,他的所有 心思都用在了如何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上,所以他才能够以自己的实力 出现在世界影坛,并很快实现自己的愿望。 评判一部国产电影的优劣高低,或者是否“纯粹”,居然不看其表现内 容、制作水准、艺术质量和创新度,仅仅追究其资金来源是“境外”还 是“境内”,实在有些让人啼笑皆非。这让我想起一件事,中秋节前媒 体报道某些个体小作坊用变质原料生产劣质月饼,被我们的工商部门检 查出来,尤其令人恶心的是,这些小作坊不仅用料伪劣,某生产环境更 是难以目睹,蝇飞蛆爬、老鼠蟑螂四处横行……然被检查者还振振有词:我们缺乏资金。如若按照金鸡奖的评选理论(或规则),这就完全可以 原谅了,也是“不必小题大作”,因为那些在企业奖金,星期三能外资。 刻前几年“进口大片”刚刚出现的时候,就有人对美国人拍摄《真实的 谎言》用了相当于十个亿的人民币而大发感叹,但也有影评人反问“给 你十个亿,你就能拍出《真实的谎言》吗?”我很赞同这各反问,因为 谁都知道奖金总是决非电影伤口水平高低的本质因素。抓住这一点,将 一些优秀的国产影片“不与国产片混同”,就意味着给落后甚至低劣以 宽容;就意味着给不鼓励讲求艺术质量;还意味着不尊重以艺术实力去 争取境外投资的艺术家们的辛勤劳动。当然,郑雪来先生提出“小题大 作”的观点,主要是针对周传基先生文章中“把国产片不景气的原因仅 仅归结为一些录音、道具问题,甚至将其提到违反‘纪录本性’的高度”来说的。的确,国产片不景气的原因很复杂,但就一部电影的制作而言, 录音道具总是果真不重要吗?明明表现的是三十年代抗日战争,却让观 众看着日本鬼子驾着六十年代的解放牌汽车在银幕上横冲直撞,这难道 还不违反“纪录本性”?(这解放牌汽车是谁赠送给日本鬼子的,审查通 过了?或者是有意表现两种势力的合作?比如说,在我国现代历史上有 过两次国共合作,何必小题大做,郑先生,你说是吗?)。有个剧组在南 京拍片,其内容是解放战争的,需要有城市废墟的镜头,恰巧那时南京 正在大搞旧房改造,有拆迁的地方都要写上个“拆”字。剧组就利用这 些拆迁的旧房拍废墟镜头,可做道具总该把那墙上巨大的“拆”字用烟 熏一熏盖掉吧,他们偏不,硬是用一个特写将那“拆”字清晰地留在了 完成的影片中。结果影片放映时,每到此镜,观众必发出一阵恶笑。好 悲状的一场戏就这样成了一种玩笑。从这一方面看,我们电影界确实有 许多人还没有学会拍电影,或者根本就不想学会拍电影。 回郑先生 周传基 (此文是未经文汇电影时报编辑过的原文,我事后还做 了一定的修改。) 郑雪莱先生和我商榷的文章辗转传到我手上,晚了一些。现在作答。 电影综合艺术论者总是不可能真正认识电影本性的。当然,这并不会妨 碍他们去读一两本有关电影本性的书籍,并且背上一两段。因此当我们 提出电影纪录本性的时候,作为电影综合艺术论者的郑雪莱先生就自作 聪明地说,周传基先生所说的纪录电影本性论,他其实一点也不陌生, 那就是安德烈. 巴赞在《摄影影像本体论》中所说的“技术应保持所描 绘的自然物的暧昧性和多义性”。然而(要知道),我所谈的纪录本性,恰恰是郑先生非常陌生的。巴赞的理论的毛病在于,那时的他还没有刨 到本性的根。而在这里,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一成不变的,至少一百 年不变的郑雪莱先生就缺乏具体分析和认真研究了,他的“研究”成了 无的放矢。 郑雪莱先生的记性确是很好,读过的书,可以过目不忘。但是对书的内 容缺少一点科学的思考能力,那就不如不读书了。要知道,巴赞的理论 是三十年前(全部历史只有一百年中的三十年)对电影本性的认识。可 是郑雪莱先生是否知道,人类对宇宙的认识是不断往前进的,否弃旧的,创建新的。只有反动的统治阶级害怕前进。对电影本性的认识也一样, 如今早就超越巴赞了。你不想前进,可你挡不住他人往前进。不仅我讲 的电影本性认识已经超越了巴赞的那个时代对电影本性的认识,法国的 几所巴黎大学的教授们讲的,洛杉矶加州大学的教授们讲的,香港浸礼 学院的教授们讲的,日本大学艺术学院的教授们讲的都已经超越了巴赞,而且不要继续超越现在的认识。巴赞是开创了对电影本性(
电影是什么) 的研究(丰功伟绩!),但他只不过是在人类用木乃伊保存自己形象上, 人类的向往上转了半天,最后并没有说到点上(也就是心理学),十分 缺乏科学的心理学因素。在六十年代末,自从大家发现了蒙斯特堡于 1918年写的那部超前的电影理论《影戏---一项心理学研究》(PHOTO- PLAY -A STUDY OF PSYCHOLOGY ) 之后,电影的本性就得到了更
为科学的解释。这是全世界( 大陆中国例外)的电影理论界人所共知的事。
(我们那保守主义的《电影艺术辞典》里愚昧无知地以一种莫明其妙的 居高临下的态度说蒙的电影理论是一种初级的认识。可是国外的电影理 论家们却非常惭愧地认为自己太愚蠢了,蒙斯特堡在本世纪初就已经说 清楚的理论问题,我们在六十年代才开始有所悟。足见在中国的《电影 艺术辞典》中写这个词条的那位先生根本就没有弄懂蒙的理论。当然, 他也实在没有能力弄懂。) 同时还要指出,郑先生声称是在和我商榷,但却在批巴赞。为什么呢?
真是跟大革文化命结束以前的几十年来“某些人”所惯用的手法一样。 先设一对自己进攻有利的假想敌,扣上一顶莫须有的大帽子,然后用大 棒朝那顶帽子猛击过去。对于象郑先生这样的人,这样做是毫不奇怪, 我们也挨了五十年了,有丰富的经验了。至今谁欣赏郑先生,郑先生又 欣赏何人(比如说,苏联斯大林的打手日丹诺夫。中国的就不提了吧) 他举出了一些所谓的实证,“我只想提一点:我国电影界其实对巴赞的 论点也不是那么盲目推崇的,因而在80年代下半期陆续出现文章指出“ 中国的巴赞热在理论上的错位”,“这种理论移植中的偏颇”,“中国 错误地再塑巴赞”,“一次历史性的误读”等等。”例子举得太恰当不 过了。他这样做证明了几件事。第一,他没有弄懂巴赞的理论,第二, 现代电影理论的研究早就超越了巴赞,第三,中国的电影综合艺术论者 错位了,大错特错。中国的电影综合艺术论者对巴赞的理论不是那么推 崇吗?这是必然的。电影综合艺术论者根本没有弄懂电影是什么,他们 根本还没有接受电影本体,也从不研究,因此谈不上推崇与反对巴赞。 说得不好听一些,是还没有资格。移植吗?危害最大的移植就是本世纪 初的意大利的那位卡努多先生所发明的“电影综合艺术论--电影是第 七艺术”。借用你们某位电影综合艺术论者的说法,是最老最老,老掉 牙的,换上新装到中国来充当新嫁娘的外国老太婆。从世界范围来说, “第七艺术论”被公认为电影理论史前史的东西,我的说法是电影石器 时代的东西。有时提提而已,它不是理论。站在史前史的立场上,巴赞 那当然是一种错位。正如一个拿大顶倒立的人所看到的整个世界是颠倒 的。所以站在电影综合艺术论的立场上,当然是巴赞理论的借位。郑先 生说,电影艺术综合性是客观存在。他连最起码的现代理论研究的方法:主观系统和客观系统的差别都没有弄清楚。请问你心目中的电影是什么,电影=商业发行放映网系统的故事片吗?电影的客观系统是什么?组成 电影这一客观系统的基本元素是什么?没有文学、戏剧、绘画、音乐就 没有电影了吗?你所说的电影是什么。中学的物理和化学课使我们学会 了研究任何问题都从元素开始。 那我们就从根上说起,这是我们在中学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电影的 基本元素是光与声,没有光与声就没有电影。如果郑先生不同意的话, 那就请他把电源拔了再看电影。光与声给电影带来的是用光和声的纪录 与还原所体现的相对时空关系。文学的时空是用抽象的文字符号来体现 的,它是看不见听不见的,所以它需要用隐喻性的描写。脱离了隐喻性,文学就不存在了。戏剧的时空局限在那假定的舞台上,它没有纪录的逼 真性,你得承认那就是战场,那就是二楼,那就是舞厅……音乐没有光,只有声音,绘画没有声音,而且是静态的。它们的综合怎么成了电影的 客观存在?是你主观地认为它是客观的存在吧!量你也说不清楚。不要 跳过去。请问雷锋这个题材芭蕾舞蹈怎么表现,交响诗怎样表现,雕刻 怎么表现,油画怎么表现,水彩怎么表现,国画怎么表现,小说怎么表 现,诗怎么表现,舞台剧怎么表现,京剧怎么表现,西洋歌剧怎么表现?什么叫美学,什么叫戏剧美学,什么叫电影美学,都一样吗?那岂不是 普通美学就够了?脱离了以媒体为基础的形式,美学还能存在吗?别搞 错了。综合是化学,化学学过没有。你能赐知戏剧与音乐怎么综合,小 说与绘画怎么综合。你知道音乐是什么吗?你知道绘画是什么吗?在你 还没有把文学、戏剧、绘画、音乐各门艺术都精通以前,你怎么知道它 们能够综合起来呢,在那方面综合呢?在你们的综合论里,有谁写过一 篇象样的,全面地谈综合的文章?谁把音乐性谈对头了的?连画面都看 不懂,还讲什么绘画性。其实电影电视作品的结构很象音乐的结构,你 们的音乐性里有谁人涉及到这一点了?我早就下了结论,中国的“电影 综合艺术论”不“综合”,谁懂什么,电影就是什么。这是中国电影综 合艺术论的特点。你口口声声说综合艺术,但你只谈了文学性,因为你 只懂文字。难道不是这样吗? 电影是一门新兴的媒介形式,一百年前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一个 崭新的,全新,完全不为人所了解的媒介形式,人们对它的认识必然是 逐步前进的,这完全符合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过程。不可能一开始就全部 认识清楚的,而且最初的认识肯定是非常幼稚的。但是作为电影综合艺 术论者的郑雪莱先生及其他先生们却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是停滞的、永恒 不变的,至少一百年不变。既然卡努多提出了第七艺术论,巴赞率先提 出了对电影本性的研究,那么谈到电影时,言必综合艺术论,谈到电影 本性时,言必巴赞、不允许再往前进。螳臂挡车。在我们看来,电影综 合艺术论,那是多么古老的的华格纳的陈旧的观念,它只不过是电影发 展历史中的石器时代(整个电影一百年历史的头二十年)的理论雏型, 它根本不够资格称为某种正式的电影理论。郑雪莱先生不是曾在一篇文 章中说,“你们年青人对外国电影情况不甚了了,”吗?那就请你说说 综合论的由来,它是舶来品,这你总该知道吧。第一个提出综合论的人 是谁,现在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的电影理论是综合论的?谅你也说不 出来。我来说吧。意大利的一位电影先锋派卡努多(Canudo)于1911 年提出电影是三种空间艺术和三种时间艺术的综合,因此它是一种时空 综合的动态造型艺术,亦即所谓的“第七艺术”。卡努多对电影的认识 的唯一合理部分正是“时空的综合---动态的造型”。而我国的电影综合 艺术论恰恰把卡努多电影观的唯一合理的部分给取消了---去其精华,取 其糟粕。这是智商问题。更糟糕的是,中国的电影综合艺术论(以下简 称综合论,因为这是唯中国独有的)不仅扔掉了卡努多的时空综合的动 态造型,而且综合论就从来没有真正的“综合”过。什么多少作家参加 电影创作,多少小说搬上银幕,等等也算是电影具有文学性的证据。这 也未免太可笑了吧。简直是幼儿园。难道你现在还没有意识到,当年, 即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电影翻译界在翻译苏联电影文章的时候,对 DYNAMISM,或denamicheski的理解是肤浅的,我们往往把这一概念翻 译成“紧凑有力的”是大错特错?爱森斯坦的理解就是“动力学”,这 是未来派的主张,没有第二个解释。事实并不会是像你所担心的那样。告诉你,如果电影只剩下影像和声音(那是电影的媒材),电影不会走向毁灭,而是会在中国获得重生。事实已经证明,你们不研究电影的影像和声音已经大陆中国的电影走向毁灭。 影像也吧,形象也吧,电影的元素只有光和声。 另外,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电影理论是综合论。连苏联也不是。你可以仔细研究一下苏联的电影理论,和中国的理论比较一下。有这个能力吗?我正是从翻译苏联的电影理论文章中悟到,电影根本不是综合艺术。
中国的电影综合艺术论者有这么两个特点。第一是扣政治帽子,在八十 年代初,他们通过一次会议,说出了这样的话:“不要津津乐道于电影 是什么,还是多考虑怎样为人民服务吧。”我的回答干脆了当:“正是 马克思首先津津乐道于资本主义是什么………”有人愿意和我讨论资本 论是为谁服务的吗?蠢!“是什么”所研究的是事物的本质。电影综合 合艺术论研究的不是事物的本质,他们研究的是“象什么”。电影综合 艺术论者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在争论的时候,极不老实。不研究事 物的本质,因为他们的知识极其有限。当你提出一个论点时,他们总是 要装着三年早知道,并不陌生,说一声“是啊,……”接着不做任何具 体分析和认真研究,就迫不及待地要进行反驳,“但是,………”这正 是郑雪莱先生和我商榷时所用的语气。当我谈到纪录本性时,郑雪莱先 生说,“是啊,……并不陌生,但是,形象……”且慢“是啊”,如果 你根本不懂光和声,也没有任何研究,那就别拿“形象”来唬人,当障 眼法。障眼法对于教书匠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什么是电影的纪录本性?谁说电影的纪录本性意味着只能纪录现实,生 活流?那是某些人在客观系统(光与声的纪录与还原)上建立的主观系 统。电影的纪录本性就是仿真的光学透镜与录音话筒的纪录与还原,使 纪录下来的视听形象符合人的视听感知经验,所以人们就认同这些视听 形象,把被摄体与纪录下来的视听形象视为同一,即心理认同。所以每 每个人的身分证上都利用具有这种纪录本性的照片,它甚至具有法律的 效用。如果这算小题大做,那你就算对了。遗憾的是,你这位认为是小 题大做的人,也不敢换掉自已身分证上的照片。这是纪录媒介的本性问 题。知道吗?公安局抓到一个犯人,先照三张照片,去国外,出关时, 边防战士要根据你护照上的照片端详你良久,验明正身。你可千万不要 和他争辩说,这是小题大做,是丢了西瓜,检了芝麻,你千万不要拿出 电影综合艺术论来和他论理。这是影像纪录带来的本性问题,不是形象 问题,明白吗?(!)全世界的人都懂得纪录本体,就是你们电影综合 艺术论者不懂。电影的纪录本性使得电影即可以纪录现实中发生的实际 的事情,也可以纪录虚构搬演的东西。不论电影里表现什么,都是以纪 录为基础。英国著名的纪录电影大师格里逊所提出的“电影美学”不是 纪实美学。我们有人尽在那里胡扯。 现在我再给郑先生两次机会装一下三年早知道,说“是啊,……但是, ……”。你我都是过来人,都算是老电影工作者了,那么郑雪莱先生知 道不知道,在大革文化命以前,在那个最没有文化的女人到中国电影界 来搅混水以前,全中国的电影制作从来都是同期录音,没有一部影片例 外。长影厂你不是去过吗?没有去参观一下它的那六个同期录音的大摄 影棚?不信可以问长影、上影、北影、珠影和西影厂的录音师和演员们,哪一部故事片不是同期录音。没想到吧?出洋相了吧?你说综合论是客 观存在,我看你就十分缺少客观具体的分析,缺少认真的调查研究。长 影的那六个摄影棚可是真的客观存在。你听谁说的同期录音费钱?为什 么全世界都认为省钱(最近电影界很多年轻人大看伊朗和南韩的故事片, 也都是同期),可你却认为同期费钱。又不客观了吧。是那些无能的人、 偷懒的人或者是想往自已的腰包里多揣点钱的人对你说的吧。开汽车还 会撞死人呢。 不要把自已的无能理论化。 这是某些人混饭吃的惯技。不会,又不肯学,可以下岗嘛。“理论家” 也不例外。 我们强调同期录音的目的是要用最经济和简便的方法来获得准确的同步 声,从而在观众心理上造成那话声不是从银幕旁的扬声器里传出来的, 而是从那无声的银幕上的人的影像的嘴里说出来的幻觉,也就是纪录本 性。这是电影美学问题。没想到郑雪莱先生却这样轻率地用资金多资金 少的问题来(谈论这个电影本性问题)暴露了自已在电影理论上,在电 影美学上的无知。这种理论落差也未免太大了吧。另外,演员不会讲话, 这算什么理由。我开始犯糊涂了,这话出自郑先生之口,他是什么人, 一般观众吗?据说他是电影理论家美学家。那么请问中国的电影美学权 威郑雪来先生,不会讲话的人能当电影演员吗?你能容忍吗,如果你懂 电影的话。看来,不仅仅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学会拍电影”,我现在有 了根据再加上一句,“我们的电影美学权威还没有弄懂电影是什么。” 告诉你,现在确实有不会讲话的哑吧在拍电影,但是,一名真正的电影 理论家是不会容忍和接受这种古怪的现象的,要与之斗争的,要口诛笔 伐,要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懂吗?被动地承认既成事实,这叫什么理论 家啊。叫投机家还差不多。不会讲话,下岗嘛。中国人口有十三亿,难 道非那几个哑巴不可。要知道,原来的演员都会讲普通话的,不信可以 问上影的老演员。现在的不合格的演员都是后期录音造出来的所谓演员,而这种中国式的后期录音全是那个搅混水的、无文化的女人搞出来的。 这类人根本没有资格当演员。从来没有听说过,哑巴可以当演员的。 郑先生反问我,“周传基同志所极力反对的好莱坞电影儿电影倒是相当 注重‘纪录本性’”。为什么郑先生非要提“周传基同志所极力反对的 …”呢,这是他的论据:你反对它,可是它用的恰恰是你所提倡的东西,你岂不是自相矛盾?这种争辨方法正是郑雪来先生的一分为二的观点所 造成的。非此即彼。我认识世界是一分为三。我不是一分为二的绝对论 者。现代物理学早就证明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三:是,否,或。没有这个三分法,就不可能出现电脑技术。差两年就进入二十一世 纪了,你还在一分为二呢。电影美学家郑先生的这句话也正好说明郑先 生根本没有弄明白“纪录本性”。他好象是在和我争辨说,你反对通俗 小说,可是那也是用你所赞赏的莎士比亚的作品所用的英文ABC写的啊。是的,一点儿也没有错。不论用英文写什么,懂得ABC是最起码的要求。好莱坞不仅是象你所说的“相当注重”纪录本性,它可是极其精通纪录 本性,而且远远比你(我们)要懂得不知多多少。但他们的知识不是来 自背什么书本上的教条,也不是研究巴赞的纪录本体的理论,而是来自 对票房(即观众)的研究。来自生意经。为什么好莱坞的影片制作肯花成 本的百分之四十到六十去买“芝麻”,从而使一些人肯花八十元人民币 的高价去看《泰坦尼克号》?简单极了。你若是明白一点儿生意经,也 许你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娱乐电影的理论家。可你现在什么也不是。 有一点请你弄清楚,我反对好莱坞电影儿,反的是它的意识形态,以及 反对有人(主要是中国人)把好莱坞电影儿看成是艺术。好莱坞电影儿 也不是象您所说的那样,雅,它是纯娱乐品(Hollywood is business, pure and
proper) 是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您有意见吗?请读读我的大学电影 教材中的《商业电影的 生意经》吧。 奉劝综合论者,要学学当代的理论研究方法。现在不论是研究哪门学科,其研究方法都必定是科学的。因此一定是从研究事物的本质入手,而不 是从借鉴其它艺术入手。没有不研究事物本质而先去研究借鉴的理论。 不研究事物的本质的工作,那叫业余方法。我始终认为综合论是中国发 行放映网系统的业余理论。他们连自已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就去借鉴。 且慢谈什么“样式混杂”,如果您研究电影而不懂本性是什么,就好象 在自已是男是女都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去恋爱!真奇怪,为什么在中国,研究一个事物的本质会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对。而且本性怎么对某些人来 说会是这么样地难以理解?告诉您,摩托车是机动车,不是电驴子。机 动车谈的是“本质是什么”,电驴子谈的是“这玩意儿像什么”。 简单地说,要研究本质,那就得研究媒材。中国书法的特征决定于它的 媒材:宣纸,毛笔和水墨。不存在宣纸贵不贵的问题,嫌贵,买不起宣 纸,那就别搞书法。简单极了。正如没听说过在麻袋片上绣花一样。那 么电影的媒材是什么呢?通过摄影机和录音机纪录下来的光和声的运动 现象。 再说一遍,我说的电影纪录本性指的是,电影这种仿真的纪录工具所创 造的银幕形象怎样激发了观众记忆中的视听感知经验,从而造成一种幻 觉,也就是一种似动现象(phi-phenomenon),调动视听感知经验的关 键性因素就是纪录的逼真性。在电影里,我们首先研究这个,也就是我 们之所以看得见银幕上的视觉形象的基本道理,而不是在电影里研究其 它艺术。连观众的眼睛是怎样看的,耳朵是怎样听的都还没有弄清楚呢,奢谈什么“形象”。唬谁?外行! 郑雪莱先生根本不懂,电影的纪录本性所带来特点之一恰恰是逼真性, 即巴赞所说的渐近线。所以他认为在电影里讲究逼真性是小题大做,是 芝麻,不是西瓜。这位电影美学家把电影本性所带来的逼真性变成了道 具。真不知他的电影美学研究的是什么。出于无知,他抓住的我随便举 出的两个实例,自以为抓住了我的小辨子,就非常得意提出来说,好莱 坞的大制作(又举好莱坞,言下之意是您所反对的那个)是追求逼真性 的,因为它有雄厚的资金。按郑先生的说法,好像逼真性的实现所依靠 的是雄厚的资金,包括同期录音在内。耗费钜资来追求逼真性是商业性 故事片中司空见惯的事。但是郑雪莱先生为什么偏偏要拿这些例子来为 违反纪录本性的现象辩护呢,说穿了,是为了维护综合论而对本性开火。郑雪来先生是经历过二战的,请问,如果在我们的银幕上出现1938年的 中国空军飞机场上有带白色五星徽号(1942年才开始用的)的美国军用机 (日机轰炸云南后飞虎队才到昆明),您该如何小题大做,如何解释中美 关系?如何明确时代。除非您有白内障。 另外,郑雪莱先生以好莱坞的制片为例,人家有钱,“可以把一连串豪 华轿车毁掉,可以把一大批真的飞机烧掉,……好莱坞依仗其雄厚的拍 摄资金和优越的科技条件……”那么请问郑雪莱先生,在中国的上海, 二、三十年代良家妇女的旗袍开衩开到多高,妓女的旗袍开衩开到多高,这些知识要花多少钱知道?现在在我们的大小银幕上出现的二、三十年 代的女主人公的旗袍开衩开得如此之高,我敢说,在当时,即便是妓女 敢穿,走在马路上也会因“有伤风化”而被抓起来。难道旗袍开衩需要 有雄厚的资金才能开得低,资金不够就得开得高吗?否则裁缝不干?! 您的那些不小题大做的电影中的人物(包括我党地下工作者)看起来都 象是妓女,您认为这是芝麻还是西瓜?还是您缺少对二、三年代大城市 的知识?再问您一句,二十年代的旗袍有短袖的吗?掐腰掐到什么程度?您可是过来人啊!好莱坞有一部影片《苏西王的世界》,讲的是五十年 代香港的妓女,你去看看那些妓女的旗袍开衩有多高。 还有一个问题。二、三十年代在中国那几座大城市的租界和欧洲各地, 包括美国在内,舞场里不兴跳三步舞(受俄罗斯文化影响的东三省不在 此列),都是跳狐步舞。可在我们的故事片中的那个时代全都跳三步舞。请问郑雪莱先生,这是不是又是资金问题。跳三步舞便宜,跳狐步舞贵?所以只有好莱坞跳得起狐步舞,我们只能跳三步舞。这是由于您缺乏对 电影本性的研究与认识,所以在争论的时候,举出了使自己大出洋相的 例子。请郑雪莱先生自已说,在我国的故事片中还有那些类似的,其至 更为严重的例子。您不妨也小题大做一次,试试看,如何?您先提,免 得我提出来后,您马上又装出三年早知道地说“是啊,……是啊,但是,……”类似的例子,我在下一篇文章中再提,多着呢。当然,普通观众 也知道不少,您如果找不出来,可以找个普通观众打听一下。 记得您在和张骏祥老师进行争论时,有一点是说的对的,您说电影是直 观的。直观,这涉及到电影的本性。遗憾的是您没做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也没有认真研究。不甚了了。估计您只是道听途说地一说而已,自己根 本没有明白“直观”意味着什么。要不然也不会有今天的这一场争论。 也正是根据电影电视本性的这一最大的特点,我们说,纪录媒介是一种 民主化的进程。这也就是说,在这种纪录媒介出现以前,只有王公贵族 和有钱有权的人才能花钱雇画家来为他们画肖像。可现在谁都可以拥有 一台照相机,甚至摄象机,连照相馆都不用去,只需手指轻轻一按, 就
获得了自已的肖像。您没有注意到吗?观众看电影时,首先的反应大多 是“像”,“不像”的问题。他们首先找的是纪录本性。 电影作为艺术,是不同于其它所有的传统艺术的一门崭新的艺术形式, 它的特点是看得见听得见的、纪录下来的运动。观众喜欢看的正是这种 运动,否则电影在发明之初就会夭折了。观众才不管您的什么影象与形 象的差别,观众就是喜欢看动。所以安东尼奥尼、费里尼、伯格曼、布 努埃尔的艺术作品中总是不乏运动。 跟郑先生讨论“解释现实”的问题,为时尚早,学英文还是得从ABC 学起。电影的ABC郑先生还没有弄懂呢,在郑先生的文章中的第一段就 反对我说的一句话:“我们至今还在电影里研究其它艺术”。我这句话 正是冲着象郑先生这样的人(也就是电影综合艺术论者)说的。 郑先生提出了纪录本性论与形象本性论之争。我从未参与过这种牛头不 对马嘴的争论。纪录本性讲的某一特殊的客观系统所包含的组成元素, 形象本性这个提法就是不研究电影客观系统的元素,而把传统艺术的规 律强加于电影,说成是它的本性。结果形象本性论只不过是用电影摄影 机和录音机把其它艺术纪录下来,就象留声机那样。电影被取消了。研 究影和声,研究电影的纪录本性不会使电影毁灭,放心吧!我耽心的是,那些不研究电影纪录本性,而且连ABC不懂人在搞电影,那才真会使电 影走向毁灭呢。您知道什么是电影的纪录本性吗?是纪录现实也好,解 释现实也好,生活流也好,超现实主义也好,都得使用纪录本性所带来 的视听语言,都得摹拟人的视听感知经验。只要使用电影这个媒介,不 论搞什么样的作品,都必须依靠电影的纪录本性,这是电影发明的原理。除非您另外发明一种“电影”。要知道,电影这个新兴的艺术是独立于 其它艺术之外的。可以借用原百老汇的舞台剧导演马摩里安在拍第一部 影片时所说的话:“我虽然不懂电影,可是我懂话剧。话剧是一门独立 的艺术,电影也是一门独立的艺术。我只要把电影拍得不像话剧,那就 是电影。”多精彩,他领会的是“不一样”,他没有提戏剧性! 可是那些既不懂电影,又不懂话剧的人就觉得两者很像。所以电影就具 有了其它艺术的属性。您不是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电影由于其与 戏剧同是一种综合艺术,同是一种通过在观众面前直接进行的场面展示 动作或事件的艺术。”可见,您即不懂电影,也不懂戏剧。同是综合艺 术那又何必分什么电影与戏剧呢?您是否知道,元素同是氢和氧,但是 二氢一氧和过氧化氢是两种不同的化合物,您敢喝双氧水吗?这是中学 的化学知识。没有这样的知识,怎么能搞电影这门科学技术的产物所带 来的艺术形式呢?另外,电影是通过在观众面前直接进行的场面展示动 作或事件的吗?综合论者的郑美学先生,别搞错了!不需要读什么高深 的理论书籍,看话剧和看电影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舞台演出是真人在 舞台上面对着观众厅里的观众,那叫演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交流,舞台上的表演者可以根据观众的反馈随时调整他与观众的关系,而电影 是真人的光和声的纪录形象出现在银幕上(是谁纪录的?),当他的表 演被纪录下来的那些时刻,没有观众在场,那叫制作,他和观众没有直 接的交流,而当观众在看他的表演的纪录影像时,表演者不在场,观众 和他也没有直接交流,这是单向交流。话剧是双向交流,电影是单向交 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论不早就把这一点阐述得十分明确了吗?读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书吗?请看,在默片时期美国就已经发现在电 影里(以下引影片中的原文)camera can help to tell the story
instead of being just the servant. D.W.Griffith used
the camera to become a master
storyteller.在默片时期,在美国Acting for film was heavily
influenced by stage acting, after all, that was the
only kind of acting that anyone had ever seen. The
two are radically different. Radically different! (
根本不同) ,而我们的电影电视中的表演那简直就是戏剧长河中飘起来的一具泡肿 胀了的戏剧浮尸。在这方面,综合艺术论是功不可灭的。 舞台的空间是假定的,那个直通天花板的舞台空间可以用来表现任何空 间,而电影银幕上的空间幻觉却是对实生活中的各种实际空间的精确而 具体的纪录,无论从视觉上还是从声音上,它都是立体的特征,包括那 混响的声音。这是电影的美学。您研究这些问题吗? 另外,我不知道郑先生为什么不谈纪录电影和其它片种。您是否知道 ,早在七十年代,具体地说,1974年,视听媒介产品在美国共计14000 项,其中只有200项为好莱坞的娱乐片。您的理论错误之一在于把商业 发行放映网系统的故事片当成是唯一的电影,当成是当代电影。所以您 会说,“戏剧冲突是当代电影的一个重要的组成因素,……60年代在欧 洲电影界风靡一时的‘非戏剧化’、‘非情节化’早已成为历史陈迹。” 电影美学家郑先生,您指的仅仅是商业发行放映网系统以票房价值为准 的故事片吧!难道你,作为电影美学家,不知道,从电影理论上来说, 商业故事片仅仅是电影这一概念中很小的一部分。您不是曾经认为电视 只是传播媒介,而电影才是艺术吗?请告诉我,有哪一种艺术形式是不 属于传播媒介范畴的。 郑先生说,“非戏剧化”、“非情节化”早已成为历史陈迹。”我不那 么看。您那是停滞的,固步自封的,保守的看法。(当然象您这样的人 在这个社会里是吃香的。他们需要的正是您这样的人。)“非戏剧化”、“非情节化”是电影艺术的探索,不能从商业娱乐片的角度来看。当法 拉第发现电磁感应时,谁能知道它有什么用?您知道电影除了商业性的故事娱乐片之外,还有不知多多少少其它的用途,包括家庭电影。你想
不想看我十岁时的电影镜头?而且这种倾向随着电影电视方面的科技的 进步不断在发展,商业娱乐片所占的比重也就越来越少了。现在的超八 摄象机要比十年前的专业摄象机不知要高级多少倍。要不要看一下我用 超八摄影机拍摄的有关电影综合艺术论者的讽刺喜剧----一个农民老大爷 把他大车前的骡子套卸了套到他新得到的小汽车前,他本人从车头爬到 车顶上坐下,他的儿子把马鞭递给他,他威风地把马鞭一挥,“加”的 一声,赶着汽车进城了!十五分钟。我拍摄到两辆汽车相撞的镜头,我 我拍到了张学良在夏威夷的张学良。告诉您,这也是电影。难道我在家 里画的油画仅仅因为没有在任何画展展出,就不算作是绘画艺术啦?您 知道不知道,在契柯夫时代有一个水彩画家的画从来没有展出过,只是 到了六十年代,苏联才把他的画挖掘出来。电影综合艺术论不仅不是真 正的电影电视理论,而且是带了眼罩,只看见商业发行放映网系统中的 娱乐片。对电影来说,其它艺术充其量是一个借鉴的问题,所以熟悉文 学的电影创作者对文学就借鉴得多一些,熟悉音乐的电影创作者对音乐 就借鉴得多一些。把话说白了,传统观念根本没有办法真正认识电影。 因为它的问世,否定了传统艺术的一切规律。艺术的发展是从演出艺术 到再现艺术,然后到纪录艺术。不管您能否接受,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 至于“纯电影”的问题。这是电影理论家研究电影的最宝贵的概念。没 有它,很难弄清电影究竟是什么。有些人害怕变,所以就耸人听闻地说 什么“先锋派的乌云出现在中国电影的地平线上,”“先锋派的乌云笼 罩着中国电影。”可我认为,中国电影先天不足的原因之一就是缺少一 个先锋派运动。二十年代搞电影先锋派的人物大都是共产党员。所以赞 成先锋派并没有什么错,而反对它的人就很成问题了。这一概念可以通 过电影时空概念的演变来认识,这自然又不是电影综合艺术论者理解力 所能及的。自1979年以后,继而于1981年出现的MTV(中国特色的MTV 不在此列),纯电影的概念就进入了商业电影,而且成了可供消费的商 业广告的重要内容。这在我的大学电影教材中的“电影相对时空结构” 的讲义中论述得十分清楚。 您的全文只有一句话是说对了的。“电影学院近十多年来培养了那么多 的人才,而您说‘还没有真正学会拍电影’,那您岂不是否定了自已的 教学。”没错,事物是不断在发展的,认识是不断在深入的,更何况电 影是一门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媒介形式,它是那么地年轻。难道您没有看 到,电影这一百年来不断地在变化,人们对它的认识不断地在改变,( 只有您们综合论是停滞地一百年不变)我告诉您,巴赞的丰功伟绩不在 于他的具体的观点是怎样的,而在于他开始了前人所没有做到的--对 电影本体的研究。不是巴赞错位,是您们错位。当然,我们不知道蒙斯 特堡早在1916年就开始了对电影本体的研究,而且比巴赞要准确得多。 我们在蒙斯特堡面前感到惭愧。因此为什么不该否定自己的教学成果。 我不是那种丧心病狂的、常有理的、停滞、保守的、靠某种势力生活的 人,我从来不是那种认为自己没有错的人,而且谁要说我有错,我就会 认为那人就是反革命。这是虚弱和卑鄙的人才会干的事。有人干了一辈 子。但不是我。 我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改变,我总觉得有一些新的认识没有讲给前一个班 听是一个遗憾,而且我总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我的不足,正是因为某一 点我自己没有认识透彻,所以没有给他们讲清楚,因此他们就拍成这样。我认为只有不断地否定自已(而不是一成不变)才不致于象电影综合艺 术论那样成为电影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或绊脚石。 更何况在电影综合艺术论如此猖獗并泛滥成灾的中国电影教育界,只有 我一人公开坚持研究电影本性(真是怪现象),那更需要有自我否定的 精神。我从来不害怕否定自已,所以才能把陈腐的观念和理论远远抛在 后面。不过请放心,我再怎样否定自已,也不会倒退回到石器时代的电 影综合艺术论。 同时也借此机会告诉一些好心的年青人。您们总是觉得我还在与电影综 合艺术论作战是多余的。不止一位年轻人跟我说过,电影综合艺术论早
就被否定了。可是您们看一下,电影综合艺术论不仅存在,而且还有市 场。郑雪莱先生,他可是公认的电影理论权威啊,还在说,“电影综合 艺术性是客观存在。”尽管他自已也说不清楚,也说不具体,那综合性
都是什么。他只说了文学性。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是不是在我们北京 电影学院和广播学院,电影综合艺术论还盘踞着相当大的地盘。 如果您硬是不想遵守电影本性的规律,那也没有关系。观众不看,您也 没辙。八十年代以来,当人民的娱乐项目越来越多的时候,个人娱乐开 支的分配就出现问题了。电影再也不是唯一的娱乐项目,“独此一家, 您爱看不看”的垄断时代已一去不返了。还守着电影综合艺术论不放, 那就准备着把观众丢光为止吧。 另外,《怒火之花》怎能与《公民凯恩》相提并论?《公民凯恩》怎么 会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它是现代电影的里程碑,它推翻了清教徒那 骗人的一分为二的、黑白分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论,它证明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三的。所以我们认为这部影片是现代电影 的开端。我不知道您的“当代电影”指的是什么。而《怒火之花》却是 那位正统的右派导演约翰. 福特根据美国共产党作家斯坦倍克根据马克 思的资本论所创作的一部杰出的经典小说《愤怒的葡萄》庸俗化为好莱 坞的家庭情节剧。至于《一曲难忘》和《居里夫人》,我相信电影美学 家郑先生回味起来确实会其乐无穷 文学创作讲究修辞学,您的译文也十分讲究修辞学,我从您的译文学到 不少东西。可您知道不知道,电影的视听语言也讲究修辞学。现在我希 望您下一次从综合论的角度讨论一下关于中国电影九十年来有哪些故事 片在视听节奏中对特写镜头的运用是及格的。并请对您所选中的那个段 落从修辞的角度做逐个镜头的具体分析,和认真研究。 十年的争论?您也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而不是“不想说什么了”)。电影综合艺术论者怎样也搞不懂巴赞的电影美学的。.“‘电影艺术综 合论’研究有方?文学性搞得好?”且不去说它,我不明白,为什么要 “且不去说它。”我正希望您去说它。这是关键,因为当您一开始去“ 说它”,您当然想说得全面,于是就越说越乱。不信您写一篇全面的论 述电影综合艺术论的文章试试看。不要躲躲闪闪的。我在这里等着批您 的文章。建议您读一下我的教材的第三章:综合艺术论不成理论后面的 附录早期电影理论的批判史(美V. F. 帕金斯著)的译者必不可少的的话,
大约有三万多字,主要是针对您的这种观念写的。这样您那未来的那篇 文章可能会更全面些。 另外我还等着要求于您的那篇具体的分析文章。 最后,我需要强调指出,舒克先生的文章写得非常精彩,理论水平比您 我都高,真是后生可畏。看来您我很快就会被这样有为的年轻电影理论 家所淘汰。这是可喜的规律。电影理论阵地早就该由这样的年轻人来占 领了。可您们还在把石器时代的东西塞给年轻人,作孽啊。看来,再不 能让电影石器时代的综合艺术论混入二十一世纪,让世界耻笑我们中国 的电影理论。正如美国某大学的电影系系主任说的:“You put everything into
cimena, and cinema is not cinema." 噢,还要提醒郑先生一句,我研究的问题不是局限于商业发行放映网系 统的故事片,我研究的是电影(CINEMA)。 周传基 于旅美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