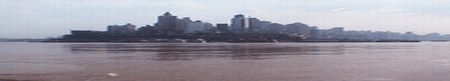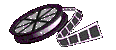(二)电影的过去时态
1、回忆的过去
在《野草莓》中,伯格曼在引导观众从现在时态进入主人公过去回忆之中所采用的方式是极其精彩的。故事是关于七十六岁的医生伊萨克·鲍奇一天中所遇到的事情。这天他驱车从斯德哥尔摩到一座大学城去接受荣誉学位。这天的旅行变成了他生活的旅程,他既在许多场合遇见了和他现在有关的人们,又在回忆中遇见了过去和他有关的人们。在下述场面中,他访问了自己青年时代乡村的家。他不知不觉地陷入了青年时代所渡过的许多愉快的暑期回忆---回忆起他和他曾经爱过并失去了的那个姑娘在一起摘野草莓。
我们看见年迈的鲍奇博士望着那空荡的、用木板把窗封起来的灰色避暑山庄。然后直冲着我们传来他思想的声音,我们听见他说:“我不知道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可每天清晰的现实却……”我们听见远处传来钢琴声、又再次看见那座房子。这次是打开了的,在阳光照耀下显得干净而洁白,四周是一片葱郁的草木丛。他继续在画外说:“幻化成我梦幻中更为清晰的。”背景上,混杂的钢琴声和欢快人声从敞开窗户中飘荡出来,欢笑声、脚步声、孩子们的喊叫声、水泵的吱呀声,最后还有个浑厚的男高音歌声。尽管声响是这样的活跃,但我们所看到的那座房子却不见一个人影。然后我们又看见鲍奇博士,他依然面对着我们;当摄影机缓慢朝他推近时,我们又听见了他思想的声音:“我不知道这是梦还是回忆,但它象真正的现实那样出现在我的眼前。”然后三个表现景物的镜头—瞬息即逝的又仿佛不知从记忆的什么角落里涌现出来的一株小树、云彩、以及一片野草莓。最后我们看见他曾爱过的姑娘在地上采集野草莓—我们完全陷入了他对过去的回忆。当我们再次看见伊萨克时,是从上往下看到一个可怜老人被包围在一个令人心酸的草木茂盛的世界之中,在这里他只是个多余的陌生人。
伯格曼以一个走进冰冷水里的人的那种畏畏缩缩的谨慎心情把我们带回到他的过去。每一步都经过细致的描绘和探测然后才迈出第二步。贝格曼把解说词、环境音响和视觉形象准确地加以结合,不仅有条不紊地把我们带到了过去,同时还把那可怕回忆的痛楚而又战战兢兢的过程戏剧化了。他作为一位能工巧匠的细致手法在这里用来表达了他作为艺术家的观点。鲍奇博士追溯他的过去的那种谨小慎微的、几乎是战战兢兢的方式由贝格曼极其细腻地表达了出来,并把我们带进其中。
这一段落的回忆变成与过去的遭遇,而不是沉浸于过去。鲍奇博士从来没有失去自己作为老人的身份,导演始终没有让他完全卷入回忆之中。在大多数镜头中,他和他所回忆的那些场景是隔开的或者保持了一段距离。但是甚至当他没有出现在视觉形象中时,当他的过去充满了银幕时,我们也没有感到是完全投进了时间的过去之中。那些纯粹代表鲍奇博士青年回忆的视觉形象所体现出来的直接性,经常与我们看见他这个老人的客观景象混在一起。于是现在时态变成了一种混合物,通过照明、化妆和服装,过去和现在在同一个段落镜头中分别地加以刻划。鲍奇博士的世界变成了他一生的期望和挫折的视觉体现。当他和那过去的象电击般的视象相对比时,他就象一根被海潮冲上荒芜沙滩的屈节漂木,显得分外苍老和可怜。他对自己美好青春的怀念始终带一种悔恨的情绪缠绕着他的生活,但最终把他封起来的不是他的过去,而是他的现在。最后通过他和自己那无法摆脱的过去心酸而实在的形象的遭遇,被戏剧化了的正是他那隐隐绰绰、瞬息即逝、和脆弱的现在。过去终于成为面对他的一面嘲笑的镜子,把他摆进了虚度的时间、摆进了被弃置和无结局的时刻。
贝格曼运用电影固有的可塑的现在时态的可能性来处理过去,只从中抽出鲍奇博士一生中关键性的因素,并且最后把这些因素巧妙地纳入了鲍奇心劳神疲地对自己身分进行探索的结构之中。过去成为现在的不可分割的方面,它以一种新的意外事件所具有的那种新鲜和变幻莫测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眼前。
然而通过对过去回忆的诱导来说明现在的做法并不一定要像《野草莓》的场面那样精心设计才能生效。几秒钟的电影时间就足以回想起关键性的过去,从而改变现在的性质。在雷乃的《广岛之恋》中,过去如此接近电影现在时态的表面,以至它可以从女主人公内心深处涌现出来,溅泼在银幕上,然后再次沉没,通过加深我们对其中意外因素的了解而改变了现在。
女主人公来到了广岛,在一部和平主义的影片中扮演一个角色。她没有名字,因为她的身分最终是由那构成人类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众所周知的事件的瓦砾中沉淀出来的个人回忆的总和。她遇见了一个日本工程师(也是无名无姓的)并且爱上了他,这个工程师在大战期间曾在日本军队服役。他们的关系使她回想起自己年轻时在被占领的家乡奈维尔和一个德国士兵的暂短的恋爱悲剧。在影片的前一部分出现的这一场面是她对自己那压在心头的过去的一次遨游。她的情人的手(仔细地加以照明从而立即引起我们和她的注意)引起了她对那过去的德国士兵的回忆。闪回来得突然而意外----这是由于看见那支手而激发的一种不由自主的神精质的痉挛。这残暴的视觉形象只持续了几秒钟。但在这几秒钟之中,她的生活展现出来了。这一过去真切而痛苦。它再次变成了肉体的创伤,她不得不看见每一个伤口,并且在回到现实中来以前把它包扎起来。
和《野草莓》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直接被抛回到过去,丝毫没有现在时态的中介来引导我们。但是我们并没有失去时间感。这个闪回的作用非常清楚,这不仅因为它是从一个细节切回到另一个细节,而且因为这一场面的剪接节奏把闪回纳入它的结构之中。当这一场面展开时,它渗透在切换的节拍之中。当她望着他睡在他们的床上时,镜头在她和她的情人之间来回切换,形成了剪接的节拍。雷乃还通过他那惊人的开场镜头为我们准备了这一时刻,在开场的镜头中两个情人光滑的赤裸肉体充满了银幕,它又和纪录片中的原子弹爆炸后广岛人的那遍体的实际身体交叉剪接,最后叠化和抽象为在原子尘伤害和抚摸下的两个情人的肉体。而在这些视觉形象里那日本情人重复地说:“你在广岛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看见。”而每次她都接连说:“我什么都看见了。我什么都看见了。”这个开场戏是纪念碑式的,雕象式的和永恒的。这两个人物被回忆结合在一起,同时又把他们隔离开来。我们开始感到他们的一致性存在于他们过去的那些片断之中。当我们终于看到过去出现时,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它是从影片的结构中有机产生的。
2、客观的过去
当然,过去时态,在影片中不一定是回忆。不少影片使用闪回作为讲故事的简单叙事手法。但一旦闪回从客观角度来表现,从全能的角度来推进故事线索,我们势必把其中的动作看作是“现在”发生的事。它一出现不久,过去立刻变成了现在,而闪回结束时我们一般都会感到愣了一下,于是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未来,又在和一个新的现在时态打交道。为此,作为回忆的过去以及作为期待的未来都较易和影片的节奏融合起来。这两种主观视角都是直接的现在时态的两个方面,并且扩大了我们对内容的了解,而无须脱离人物生活的重要时刻。
在技巧高越的电影创作者手里,甚至客观的闪回也能有机地参与人物生活的进程。在《未婚夫妻》中处理高超的开场戏中,艾尔曼诺·欧尔米能够在一瞬间回到男主人公的过去,以透视般的客观性来表现它,然后继续叙述故事,既没有扰乱主要动作的情绪,也没有破坏其节奏。这一中断和闪回的标准用法无甚差别,它扩展我们对人物生活的了解,同时没有把动作在时间上往前推进,但值得注意的是,欧尔米能把这种了解和男主人公在我们被抛回到他过去的那一瞬间所感到的若有所失和深陷罗网的情绪融合了起来。当我们离开主人公回到他的过去时,导演并没有使我们脱离现在的时刻,主人公的过去是用来体现那驱使他前进的、强有力的、无声的冲动,银幕上的过去和现在的直接性,在这里是用来把主人公生活中分离而又有联系的两个时刻交织在一起了。
影片表现两个订了婚的男女,穷得无法成婚。那个男子为了挣得他们所需要的钱就接受在西西里岛偏僻地区的建筑工作。这对未婚夫妻必需分别数年,那姑娘感非常凄凉,因为她担心这件事终究会意味着他们的关系的结束。那个男子知道没有其它出路,他必须忍受分离的寂寞。影片开始时,这对青年男女在一座平凡的舞厅里。当他们在谈话接着又跳舞的时候,两人都反映出对迫在眉睫的分离所感到的紧张。
因为他要远行,所以必须把他年迈的父亲安排在养老院。这一段落回溯了他和养老员的谈话。虽然这个场面是由那个男子想起他父亲而引出来的,然而闪回的处理却是客观的,具有一种半纪录性电影制作的风格。我们听见那个官员安慰了他几句,然而我们通过一系列对位的画面看出这些话是空洞无物的。这些画面并不吻合那个男子所看到的。倒不如说,它们激起了他的痛苦,使他因为准备把自己父亲送到养老院而感到罪过。养老院里老人的画面就是对这个养老院的腐蚀性气氛的一种冷静、淡漠,和极其筒略的研究。那个官员介绍他管辖下的那些人最终的下场和毁灭时所使用的呆板语言刺穿了那些孤独老人的平静画面,并且引出了那个男子必然要感到的痛苦。后来当那个姑娘问:“以后怎么办?”的时候,我们突然在一瞬间又回到了现在。接着我们突然被抛进了一个新的现在时态,我们看见那个男子乘坐的飞机起飞前往西西里。影片后一部分表现的是在西西里的男人和在米兰的姑娘的事情。
主人公的过去是如此接近动作的表面,就象皮下扎了一根木刺,无需作任何准备就能拔出来。过去时态被安排成仿佛是一个隔离的事件,它完全是独立的,是冷漠的分析。它更象是一个纪录而不是回忆的具体体现。然而它所留下的伤痕却是和故事以及我们对人物的理解有机结合的。当我们回到现在时态时,我们只逗留了一瞬间,仅足以使过去的暗示,那个男子放弃责任的残酷性和它所将要带来的损失,浸透在这一瞬间之中。然后,随着喷气飞机引擎的冷漠的呼哨声,我们投入了影片的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