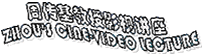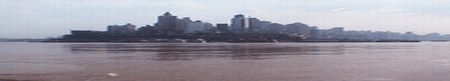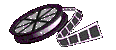第二节 电影剪辑中表达时间的惯例
从电影实际制作的角度来看,各种摄影机角度的交叉剪接使导演能通过一系列不同视角来表现一场戏,而无需延长它的时间。如果不用切换,那么摄影机运动和谈话就是在实时中进行的,从远景移到特写,然后绕过人物来获得反向角度的反应镜头的时间长度将会是不中断的实时。这是两种不同的效果。
观众一旦接受了这种空间跳跃的逻辑,他们就很容易并且毫无疑意地接受各场大加剪接的对话。试举一例,在《一千小丑》中表现叔侄谈话的场面长达三、四分钟。这是一段完整而短促的谈话;但是每出现一次切换,这一场面就完全搬到另一地点。在这几分钟的过程中,两个人物是在纽约相距几英里的不同地区进行谈话的。由此可见,那种最拙劣地模仿话剧的台词是绝对要不得的:(面对着越来越近的敌坦克车)甲:小王,把手榴弹给我。 小王:干什么? 甲:快!
我们甚至能够接受阿·雷乃的《我爱,我爱》的剪接方式。在影片主要部分,每个镜头都发生在主人公生活中与前后镜头完全不同的时间中。主人公陷入了一架试验性的时间机器,每次切换都把他带到过去的不同时刻,只有在每个镜头的长度之内时间是连续的。每一切换都把那使他陷入其中的折磨人的机械装置戏剧化了。他的生活被分割成令人痛苦的孤立单位,并且完全是通过这些反映实时的连续空间的片断揭示出来的。当切换把空间打断时,主人公就发现自己又被投入另一新的地点,这可能是他过去生活过的任何地方。
那么任何这种切换的意义就在于,只要这种切换不令人生疑,每个镜头的空间都不再在时间上相互联系起来。一旦空间中的物体,也就是时间中的关系,不再是固定了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通常对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的感觉。影片中的切换立即通过空间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新的视野,而这个地点可以是任何地方,因此也就可能是任何时间,由于空间不再是连续的,时间了就无法加以确定。这种无法确定的特点也就是电影中处理时间的关键,因为对现实的最“写时主义的”表现也把那现实变成了新的东西----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体验的那个世界没有多少联系的另一个世界,一个现实的幻觉。时间终于摆脱了我们正常假设的重压,它终于能够从节奏上和表现上来加以观察,这两个因素加强了,甚至创造了那个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场面中的戏。
这种对优秀剪辑的独特反应实际上是一种幻觉---一种视听感知的心理活动。我们已经习惯于把不同摄影机位的镜头联在一起。对于那些看电视长大的人来说,这种幻觉习惯几乎是从他出生时就开始了。
尽管有一套使动作流畅的视听幻觉技巧,影片还是迫使我们以大大不同于正常情况的方式来看电影。电影世界主要是不连贯的。例如,在生活中即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视野中某个细节上,如果视野的其他部分发生变化,我们视野边缘至少会意识到。可是在电影分切镜头中,我们虽然可以从观察细部的镜头回到全景,但是动作已经前进,把我们带到一新地点。我们接受这种改变,因为电影的叙事省略是通过光波声波不断取消中间区域并压缩时间,而光和声却又给人以连续感。
同样,我们在实生活中从来没有像雷诺阿的《游戏的规则》中所表现的那样来观察一场对话,先是从一侧,然后立即跳到另一侧。但是电影始终是这样做的,我们学会把这种突然的变化仅仅看作是相当于我们在实生活中经常变换注意力,但是在生活中,当我们暂时从观看一个场面的一部分换到另一部分时,我们仅仅变换了视野,并没有改变观看动作的地点。然而在影片中,每个瞬息的变化都不仅向我们提供了动作的另一视野,而且还提供了观察动作的新视点。不过我们却不把那个切换看作是地点的改变,而只当作重点有所改变。这也是那一成规的一部分。
电影已问世这样长久,以至我们忘了观众并不总是能够把剪接中违反视听感知经验的约定俗成的成规看作是自然的。我们可以到我们文化以外去寻找那些不习惯于现代电影成规的观众。I. 蒙塔古在他那本书《电影世界》中提到在中国就有这样一批观众。中国人会拍摄相当复杂的影片,但是为外省观众所拍摄的影片的动作依然要像在舞台上那样来表现,尽可能少用切换,“进入房间的人,必须打开门,走进去,横过整个房间----我们一直跟着他到达房间的另一端。”剪接有意保持在最小数量,因为“当你为六亿五千万观众制作影片,而其中只有五千万人看过电影,那么如果你认为对于早就习惯于电影的人来说已成为第二天性的成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却需要一些时间来习惯的话,那么你是正确的”。蒙塔古的这一观察恰好说明在那个时代,不仅中国的电影制作者,而且连他本人,以及引用他的这番话来证明电影语言只不过是一套成规的著作的作者都没有认识到电影语言的基础是以人在生活中的觉视听感知经验所产生的幻觉。
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入门的观众。看电影是不需要学习的。所以问题在于我们这一代经常看电影电视的观之中依然需要打破他们通过过去观看的影片已经习惯了的那种单一的叙事成规才能接受新的表现手段。让-吕克·戈达尔的《精疲力尽》于1959年发行时,它以破坏传统叙事的电影时空结构袭击了观众,使他们感到目瞪口呆。但是经过一代电影制作者的不断努力,观众已经熟悉这种表现手段,现在,观众对《精疲力尽》中那种极端的跳切剪辑方式已经习惯,并认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甚至几乎是天衣无缝的。
直到目前为止,对于电影制作者来说已经发展为不可改变的规律的那些惯例就是,不论时间在一场戏里压缩到什么程度,动作必须始终保持一种幻觉,仿佛它是发生在我们称为实时的那个连贯流程之中。正如中国的外省观众要求演员一进入房间,就必须看见他走完整段路一样,西方观众也要求演员至少看起来象是横过了房间。这一“透明的”流畅手法允许在不考虑空间的连接的情况下从一个拍摄度切至另一角度,只要保持连续时间的幻觉,只要动作发生的空间看起来并非是不合逻辑的中断,时间看起来就会是连贯的,观众也就接受了。最经常用来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法就是反应镜头。一个动作开始了,然后我们切出去观看那个动作造成的反应,当我们回到动作上来的时候,它已经前进到另一新位置,却没有使我们注意到那取消了的一段时间。
让我们通过J·斯科里莫夫斯基的《离别》来看一下这一技巧是怎样作用的。在这场戏里,我们看见那年轻主人公在汽车展览会上吹鼓一个纸袋。然后恶作剧地在一个姑娘后面把它击破。接着我们从年轻人那里切出去看到他的女友的反应,当我们再切回到年轻人时,他已经在新地点疯狂地击破一个个纸袋。如果取消他女友的反应镜头,观众就会感到时间极不自然的变化。那年轻人仿佛一下子从一个地点跳到另一地点。可由于我们无法估计他从第一个镜头到最后一个镜头走了多少路,因此也就无法准确感到那姑娘的反应镜头有多长,而仅仅简单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即所花的时间长到足以使他横过展览厅。
再次提请注意:当人们不假思索地使用“惯例”这个概念时,有两个解释。一是,惯例指的是约定俗成的成规,这是错的。一是,惯例指的是摹拟视听感知经验的表现手段,这是对的。所以说,“惯例”这个词应从幻觉来理解。要知道,蒙太奇是从时间开始的,也就是说,蒙太奇手段是从时间上把若干镜头连接起来。传统艺术中有绘画、雕刻等空间艺术,那是静态的空间艺术,所以传统艺术家对空间十分熟悉,并积累了深入的研究。当电影这一门崭新的表现形式出现时,因为它是活动的,亦即,它有了时间因素,所以人们必然首先对这个新的因素发生兴趣,首先研究这个新的因素所带来的特点。蒙太奇理论出现在巴赞的空间理论之前正是这个原因。
但是,我国的“电影综合艺术论”不研究电影的光波声波所体现的时空,在很大程度上还不认识电影的时间特点。所以对于年轻的电影工作者,这也是一全新的课题。需要认真的研究。请注意一点,由于视听语言在国外并不新鲜,也没有人否定或反对,因此他们在论述时,有些问题就作为理所当然而忽略过去。读者应随时记住,电影电视的时空是通过光波声波体现出来的,而不是通过文字体现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