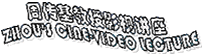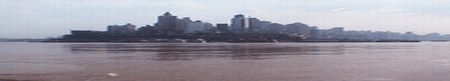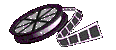十六、声音空间
声音的空间特性 我国电影电视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工作对声音的认识处于极其落后的状态。落后于世界千余年吧,不说远的,他们对声音的认识至少比不上就在我们身边的天坛的回音壁的创作者们对声音的认识。尤其是近年来普遍实行的所谓后期配音(而不是真正的后期配音)的荒唐做法(连电视剧和一些音乐节目,还有个别外语教学节目,或作为法律根据的审讯用的纪录片,居然也搞后期配音),以及长期的瞎胡闹的后期配音的做法给我国的电影电视创作者(至于那些所谓的电影电视评论家和理论家们,那就别提了!面对着那些后期配音的膺品在那里摇头幌脑地评奖呢,精品,精品!?也不怕人耻笑。他们是搞电影电视工作的吗?)所带来的对生活中声音的无知,使我国的电影电视中的声音处理堕落到了使人难以容忍的地步。难道又要象MTV 那样,向世界宣布,这是中国特色的电影声音?因此在谈到声音空间的时候,我不得不首先花些篇幅来谈谈 初级中学 的物理教科书中的声学 问题。并且希望通过对声学的研究,会使那些“电影电视”工作者悟到,原来在声场里才能真 正找到电影电视的声音的艺术特点。有人批评我说,要说服人,不仅应该摆事实讲道理,而且措词应当委婉些,让听者可以接受。说老实话,我并没有想说服现在这帮“电影电视”工作者,包括电影学院和广播学院的一部分 教员在内。我想的是,他们已经沦落到必须淘汰他们的地步,然后另找一批视听没有残疾的人,或者说,应该对电影电视界所有的人进行一次耳和眼的体格健全检查的筛选工作。怎么会有那 么多的晴光眼、白内障、耳聋和听觉障碍。对电影电视声音的研究本应是在承认生活中的声音这一基本特点的共同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声学教科书中,声音的传播所首先考虑的就是声场。声场,从电影电视的角度来说,就是声音空间。
电影电视广播的声音的真实性 在电影电视里,声音的特征是随着录音设备和技术的逐渐改进才得以逐步实现的。但是要从理论上充分认识到声音的表现力,却不是那么容易的。首先电影电视理论家和美学家的听力必须健全。
他们也没有能力动脑筋想为什么那些理论家却不吭气了呢。这是他们论理的惯技。对他们有利的,就大喊大叫,对他们的观点不利的,就装聋作哑。电视界的某些人士也没有能力动脑筋想一想,国外电视界所说的“SURROND SOUND”是什么东西。
你们可以设想。巴顿是在一个大仓库里说话,而且那句“你们听见我说的没有”是在远景里说的。为什么要用远景,因为我们知道,话筒离声源越远,反射声进来的越多,混响越强,而这混响是一个大仓库的混响,它大大加强了巴顿话声的力度。当他说最后一句关键性的话时,他出现在半身近景,这样混响就比前一个镜头弱了,可是演员的嗓门提得更高了,而且视觉上的加强也加强了这句话,于是导演又一次用声音和视觉的手段塑造了巴顿那三突出的大于生活的形象。
另外,影片两次重复表现了凯恩的妻子苏珊的歌剧演出的失败,也是充分利用了空间。第一次是从凯恩的好友李兰的角度来叙述这一事件,当幕启时,摄影机面对舞台慢慢上升,苏珊那单薄的歌声越来越远,当摄影机升到天桥上的两个舞台工人处时,我们只是隐约地听见下面传来空洞的歌声。
要知道,从单声道录音来说,只有远近之分,没有上下左右之分。可是《公民凯恩》却做到了上下左右之分,其实这正是幻觉的作用。如果摄影机不是向上摇,而是向左或向右摇,那么观众受到摄影机运动方向的暗示,认为那越来越远的声音是向左或向右去了。这个实例所表现的实际上的声画结合所取得的幻觉效果。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我们讲到这里了,依然还是在谈幻觉作用。
我国电视剧《走向远方》(1984)在有一场体育馆里谈心的段落。创作者为了强调两个人物内心的情绪,特为选定了这一空荡的体育馆,利用它的空间混响来加强两人的声音,赋予人声以特殊的情绪气氛。这场对话本可以发生在任何场所,创作选定这一特定的场所正是从视觉的光影,那面镜子以及它的声音的空间混响出发的。尽管在声音质量上沿有可改进之处,但是创作者有空间声音上艺术追求在我国的电影电视创作中是少见的,难能可贵的。它取得了称为艺术作品的资格。那些后期配音的玩艺儿只不过是一些艺术膺品而已。
在另一处是她的儿子在这个教堂举行婚礼,管风琴和合唱队的宏亮的声音使教堂里充满了隆重的气氛。
女歌星在巴黎首次演出她那优美的歌声充满了大厅,观众的掌声震动了整个大厅;在影片的结尾女歌星只身来到空旷的音乐厅向巴黎告别她的歌声在加响强烈的空荡大厅里显得那样的孤独。
声音的远近配置关系 声音在声场中的距离、方位等所造成的关系可以称为声音的远近配置关系(在视觉上称做透视关系)。录音设备是纪录工具,在实录中它必然要体现声场的远近配置关系。所以电影电视创作在设计空间调度时,要考虑这个关系。如果用后期配音的方法,那就不仅需要有事前的设计,而且在配音时还得准确地把设计体现出来,这几乎是难以办到的事,除非是粗制滥造,滥竽充数。这倒是目前我国电影电视创作的的现状。
无限连续的声音空间 这是有声电影中一个极其重要而又有争议的因素。声波传播的特点是辐射型的,亦即全方向性的。它就像一个石子落到水中激起的水波那样,一圈圈地向四面八方扩展开去。我们双耳接受外界声音的特点也是全方向性的(如图所示)。因此,人对外界声音的感受是一个无限连续的声音空间的效果。人眼可以闭上不看,或者把视线躲开,而人耳是闭不上的,它只有滤波的作用。一天二十四小时,始终不断地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入我们的耳中,甚至在睡觉的时候,我们也是由于外界噪声的干扰而不能入睡,或者被声音惊醒(当然,光也有这个作用),声音还会进入梦乡。
声音与画框的矛盾 画框框不住声音,画框是为有角度的视觉准备的一个空间限制,它无法限制全方位的声音。在电影电视空间中的声音问题上,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认真地对待的,这就是声音与画框空间的矛盾。
对声音空间特征的错误认识 在有声电影的初期,由于录音设备和技术的原始状态,电影尚不具备精确地塑造空间的可能性。习惯于传统文艺的人错把这一技术上的暂时落后当成是这门艺术所固有的局限性。同样,出于技术上的原因,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对声音的认识不足,对话泛滥成灾,主宰着一切,使电影沦为舞台对话艺术的附庸。
画外空间中的声音 该书对声音的认识的症结在于,巴拉兹对现实中的声音极缺乏认识,另外他是从视觉的角度去看待声音的。例如他说:“声音是看不见的....就空间而言,声音是性质相同,可闻而不可见的;这就是说,在同一空间的一切部分,声音的性质是不变的”,(见中译本第39页)“所以,就广播剧而言,它在形式上根本性难题之一是:光靠声音无法表现空间,因而也就无法表现舞台。”(见中译本第198 页)“可是物象的形状有许多个面:左面、右面、前面和后面。声音却没有面,谁也无法知道一段声带是从哪一面录制的。“(见中译本第199 页)”声音没有形象。银幕上的声音并没有改变声音本身原有的各种特质。原来的声音跟经过制作和还音的声音,不象真实的物象跟它们的摄影形象那样,会在大小上和真实程度上有所差别。”(见中译本第201 页)“录音师的工作只是录音和还音;他不能通过视点或角度,把自己的主观想法灌注到声带里去。”(见中译本第200 页) 既然摄影机的原理是从视觉上摹拟人眼的视力,那么录音机的原理是从听觉上摹拟人耳的听力,这有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