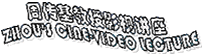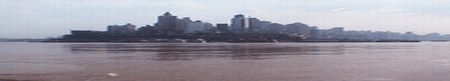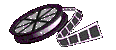十四、我国第五代电影创作者的空间观念(修订版)
我们第五代,也就是北京电影学院78年入学的那一批学生的空间观念与他们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先从《黄土地》说起,然后再回到《黄土地》之前的过程。《黄土地》完成之后在学院首次放映,对学院是个很大的震动。我记得从放映厅出来,有同学问我这部影片怎么样,我只回答说,没有好莱坞。至于其它方面我还得看第二遍再说。这时我正准备随电影学院代表团访美,我想把这部片子的镜头拿去给美国学生看。但是电影局还没有通过,我告诉张艺谋,一有消息就告诉我。就在离开北京的前几天,张艺谋来告诉我,影片电影局已经通过。于是我请他立即从他们工作样片把每个镜头都剪几个画格给我。
我都没有来得及做成幻灯片,就带着一些镜头去美国了。我在北岑加州大学UCLA的
TESHOME 博士生班上给学生看了《黄土地》的一些幻灯画面。仅仅是这些画面立即引起了学生( 其是台湾的那八位留学生 ) 莫大兴趣。后来台湾的王菲林和焦女士等同学跟我把这些幻灯片讨去了。这是《黄土地》第一次与国外的电影界见面。
《黄土地》在学院放映后,凯歌,艺谋和何群三人到我家来过一次,畅谈到深夜。谈话主要是谈话间,陈凯歌很突然地把话题转了,他对我说,“周老师,将来的争论不在理论界,而是在创作界。”他说这话是因为当时理论界在戏剧性等问题上已经开始有争论,我也参与了我场争论。我问凯歌这话怎么说。他说,“不是南北之争,而是东西之争。”我对这话好象有所悟。我问他是不是指沿海和整个中国大地之争。他说是的。我说那园林是雕虫小技。是整个祖国和这园林之争。他说是的。我说,我支持你们。我至今支持他们这个观点,遗憾的是,谁知他们现在是不是还坚持这个观点。好象已经没有了,也许是为了生意经的关系。斯特劳亨在拍完《贪婪》之后,接着拍了《风流寡妇》(MERRY WIDOW),他跟采访的记者说,我要养家活口。这里我就要谈一下我们对这雕虫小技的认识。
中国的土地辽阔而美丽,可是那些封建士大夫已经可怜到完全丧失了欣赏我们的祖国大地的能力。他们要在一个小小园子的围墙里搞一个假的风景。他们把那围墙刷白了,就跟国画的背景一样。在这白墙前用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堆成一座假山,他们喜欢假的东西,这叫以假乱真,近年来特别强调这一点。山上的树木花草全都是盆景。也就是说,祖国大地上的森林他们不喜欢。他们喜欢把一棵树种在花盆里,不仅不让它自然生长,而且还要人为地、残忍地用绳子把它盘来盘去弄扭曲了,据说那是“美”。就象我小时候听大人说的,马戏团把逃荒的孩子买下来,养在坛子里,不让他长大,然后在马戏团里展出,或表演节目。大陆、台湾的祖宗是同一个。记得第一次看台湾的电视连续剧《星星知我心》,里面有一段情节:在一个闪回的段落里,孩子们的爸爸(那时还没有死)清早在凉台上摆弄他的盆景,胖叔叔出来看到,大发感慨地说了一句,“是啊,树要栽培,人也要栽培。”多么可怕!自然的他们不要,他们非要把人曲扭拐弯地弄拧了才罢休,并美其名曰栽培,培养。那曲扭拐弯的树有什么好看的!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多丑!
假山前再有一两条弯弯曲曲的小径,这叫曲径通幽。整个就象是用望远镜头拍下来的压缩空间。那桥本是交通手段,越直越好,可非要把它变成九曲桥,转了天也到不了对岸。
我太缺乏这种诗意了。这叫有意境:曲扭的山、曲扭的树、曲扭的桥。还差一个曲扭就完成了这封建士大夫的病态审美观,那就是秀才或官老爷踱着方步后面跟他的三寸金莲的小脚娘老婆逛园林,那曲扭的三寸金莲完成了这病态的审美观。
CROOKED TREES
CROOKED STONES
CROOKED BRIDGES
CROOKED FEET
这一代年青人不要这个,好样的!我非常赞赏他们。我也问过到中国来留学的外国学生对园林的感受,他们的回答是,DEPRESSED。 这就对了,中外现代年青人的感受是一样的。谁爱弘扬谁弘扬去,对我们来说,去它的!文化大革命的痛苦经历和不可挽回的时光的损失(抗战只不过八年!文化大革命是念三个博士学位的时间,可有人觉得阳光灿烂!)使他们想要在自己的作品里寻找祖国广阔的空间(物质的和精
神的)。有人非常可怜幼稚地把这种追求看作是表现中国的落后面,是反动(有人在香山编写电影大百科全书的理论部分时一致认为的)。对于某些人来说,它只明白两件事:一,有谁在表现中国的落后面,以及二,影片中的任何人物是穿着裤
子的,还是脱了裤子的。甚至有人赶时髦地说他们的这种探索是幼稚病(那是对比着娱乐片而言)!可落后面不是这帮年青人造成的,他们正是其中的受害者。过去可以赖在国民党的头上,可是大妖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是谁造成的?还不许人说。造成这些灾难和祸害的人没有事,还是舵手,而指出这些灾难和祸害的反倒几乎成为反革命?甚至有教授说,他们的这种探索是幼稚病!教授能如此幼稚吗?准是冒牌的!记得黄式显说过此话.不知是否属实,可以去问问他。别搞错了。事关重要,因为这涉及是不是文化骗子的问题。
至于那些后殖民主义者,我要献给他们专门的一章。
田壮壮的《盗马贼》之后,出于种种的原因(包括以上提到的,另外还有没有提到的), 这一代人的追求就在一阵乱棍中夭折了。真正的第五代也就结束了。在艺术作品中,任何观念都需要通过它的语言体现出来。我现在就来谈谈他们是怎样探索电影语言的。 怎么当第五代红起来的时候,许多无干的人,甚至在起初是反对他们的人都冲到前面去了?我要提一些与第五代的成长有直接关系的,可是没有冲到前头,并且至今没有人提的人物和事情。
在校期间,这一届的学生正好赶上时机看到了至少有四百部以上的外国参考影片,而且大都是经典影片。(不象现在那样几乎专看好莱坞电影儿),他们看的好莱坞影片不多,而且到了三年级已经不喜欢看好莱坞电影儿了。发展很正常。
可是后来电影学院普遍流传着这样一种看法,好象搞娱乐片就要看好莱坞电影儿,可是就没有人问一句,为什么大家看的那些好莱坞电影儿的导演们却在看经典影片呢?值得庆幸的是,78届的学生占了这个便宜。我记得我曾问过导演系的金涛,他的毕业作品的画外空间用得很不错,他的这种空间观念是从哪里学来的。他想了一想说,看电影学来的。他们是看来的,但由于是第一次看,所以自己还不完全明白是怎样受到影响的。我参与了选片和购买录象带的工作。我非常清楚,他们看的经典影片都是什么,以及他们受了什么样的影响。但是也有一些他们本该看到,或者本该看上数遍的影片,却没有机会给他们看。因为不仅电影学院这个最高学府的校址被一些商业单位和生产单位侵占与瓜分了(在文明社会里......正如徐悲鸿亲手创办的北京美专的旧校址和北京的城墙与牌楼的命运一样),而且电影学院在文化大革命前拥有的一批经典影片资料也被电影资料馆侵吞了。全是趁火打劫。电影学院的学生要看原来是本校拥有的影片,还得花钱去租!
比上不足(如波兰的罗兹电影学院),比下有余(如后来的电影学院的学生)。
我从来不小看“看电影” 这项学习,它往往胜过老师的讲课。
另外导演系的带班老师是司徒兆敦。司徒在这期间拍了一部电视剧《路》,在这个电视剧里至少有三段的画外空间用得非常出色。比如说,当周里京(人物的名字忘了)躺在草地上,跷起二郎腿在那里挖苦修路工人时(子子孙孙地修下去),导演只拍了那只摇来摇去的鞋底。整个躺在草地上的人是在画框下面的空间,平添了许多趣味。周里京在跑公路的段落里,半路停下来帮人修车时,一下子就钻到卡车底下(画外空间)去了,动作那么快,你还以为他掉出去了,由此突出画面空间的意识。而这一届班的三个毕业作品的共同特点都是画外空间。遗憾的是三个毕业作品被学院领导枪毙了两个.1986年学院代表团访美时,带去了这个届同学们的一个期中作业,叫《当我们还年青的时候》。当我们放给纽约大学的学生看时,他们都纷纷在问,这部影片为什么是这样拍的。当我告诉他们,这些年轻人是在寻找一个新的空间。这些美国学生都非常好奇。他们的系主任MILNIE说,他希望他的研究生能拍出这样的实验影片来。他在斯德哥尔摩时就向我们要了这部影片的一个录象带。(洋人看懂了,可是北京电影学院的院长却说没有看懂。可见教条主义之害,弄到连最高学府的头头都看不懂电影了。)这一届的学生毕业后,有一批毕业生分配到广西厂。不久他们:张君钊、张艺谋、何群来找我,说他们要把郭小川的一首长诗改编成故事片。要我给他们出主意。这可是难为我了。我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把诗改编成故事片。那非同小可。我没能给他们什么建设性的意见。 另外,这几个初出茅芦的孩子选了这么难的一个题材,可以想象得到,恐怕很难得到厂领导的批准。可是广西厂有一位颇有威望的“老”导演郭宝昌(北京电影学院文化大革命前的毕业生,他们都叫他郭爷),全力支持他们,所以厂里就同意他们开拍了。那时,真是郭爷长郭爷短的,没有郭爷的支持,或许《一个和八个》就不会那顺利地拍摄出来。片子成功后,好象哪儿都没郭爷的事了。现在似乎大家都把他淡忘了。郭爷似乎也没有把这事搁在心上。可我心里为他鸣不平。那些无干的人都因为写第五代而红起来了。出现了多少文章,可就是没有人提到我们的郭爷。再说一句题外话。电影学院的前院长沈嵩生(已故,不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说看不懂电影的院长,沈院长是后来接任的)是代这一届学生受过的总代表。大家可以去问当年曾参加了为沈院长退休而召开的会议的所有的系主任,是不是广电部还派来了一位代表,他在会上指出沈院长在任期间的错误之一就是支持了第五代。这话别人不说,我就敢说。(而且在这之前,我当天就听说,一位电影元老居然亲自跑到电影学院来批评沈院长的教学哲学。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念大学的时候,校园还是相当神圣的,没有人敢随便明目张胆地闯进来的。是否有便衣特务那我就不知道了。这是官方的正式的意见,有根有据,非常可贵。写电影历史的学者和研究生,应当趁那姓艾的部长还没有死的时候,把这件是搞清楚,敲定,落实,过几年就可以写进电影史了。要不然,气候一变,说不定那个批沈院长的人倒成了一向支持第五代的人了。我是积四十年的经验说这句话的。
上海的张骏祥老师,上海电影局局长兼上影厂厂长,在第五代露头之后,要亲自办一个跟北京电影学院不一样的电影学校,最后是委托上海戏剧学院代召一个电影导演班,并声称绝对不要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员来讲课。我们也一致抵制,绝对不会去给他们上课,而且我在给上戏其它班上课时,声明上影那个班不准蹭听我的课。后话是,第二年学生反了,实在办不下去了,只好到北京电影学院来讨救兵了。)再加上第五代拍摄的影片屡遭禁映,我们也就可以明确第五代进行创作的真正“语境”了。凭良心说,电影“滑蛋”的庆祝活动有第五代的份儿没有?这是不是都是事实的存在?为什么要装聋做哑,真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会出现那样一些人对第五代,比如说,张艺谋、陈凯歌的创作的得失是那么地幸灾乐祸,什么后殖民啦,什么张艺谋的神话破产啦,他们媚外啦等等。脱离了这个真实的“语境”来对第五代妄加评论,参与讨阀,这叫居心险恶,丧尽天良,有一个算一个。不要装疯卖傻。(我不太了解发表这类观点的人,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他们都有些什么来头?谁派来的?后台是谁?)现在继续谈他们的新的空间观念。当张君钊、张艺谋、何群他们完成了《一个和八个》之后,到北京来送审时,这几个年轻人又来找我,要我去看他们的完成片。据说电影局已经通过了。我当然怀着很浓厚的兴趣去看这部由长诗改编的故事片。我看完之后,他们又来找我,要我给他们提提意见。我老老实实地跟他们说,不是我给你们提意见,而是你们告诉我,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超越了我所理解的电影空间观念。于是他们就向我介绍了他们的拍摄经过。学生超过老师,这是正常的。也是当教员的人企求并引以为荣的事。在《一个和八个》里给我启发最大的就是小护士和徐科长在荒滩上的那一个段落。徐科长从上边请示回来,带来很不好的消息。他在一个近景中坐在石滩上一面摆弄那只驳壳枪一面在发愣。这时从画面外传来小护士的声音:“徐科长回来啦。”徐科长稍稍向左回了一下头(这个动作暗示观众,那声音来自左边的画外空间)。小护士接着吞吞吐吐地说,“我觉得王指导员,他不是坏人。你给他说说情嘛。”徐科长无可何地站起来向左走去。摄影机跟摇一段,接着徐科长出画,小护士被纳入画面(就停在左画框边,大半身景),她站在那里向右画外望着,我们听见徐科长远去的脚步声。这个镜头的空间处理是利用双向出入画的运动把空间溶为一体:徐科长的出画动作把画内空间延伸到画外,小护士入画则把画外空间带入画内。这样画内画外的两个空间就溶合为一了。这恰恰是我没有想到的。而象在《黄土地》中,老农一家和那战士在黄河边吃饭的那个段落,摄影机一下子向上摇到天,在底线只剩下老农的头部。然后又下摇到地,天空只剩下上边框的一线天。我记得在学院第一次观看时,全场都很震动。这个语言太棒了。它当然不象好莱坞的成规。所以很多人看不懂。后来有人,尤其是西方的电影学者做了非常深奥的解释,我都不同意,因为在这一点上我当时还是比较直接了解他们的思想的。这个上下摇摄是代表那些农民靠天吃饭的天地思想。不是象那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是创作者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反映,一个说是创作者的什么儒家思想,另一个又说是什么道家思想,一个个都想自己标新立异,弄出点儿什么玩意儿,借中国的第五代也出个名。这是法国新浪潮“被发现”以后, 国际评论界流行的恶习。当 BBC 四频道来采访我时,我着重谈了这一点,并和采访者达成协议,如果不用这一段,那就不要用我的采访。可是他们的播出节目里恰恰去掉了我认为最重要的话。这简直是狗胆包天!而那位似乎成为那次报导中心的香港女士连一句具体而有分量的话都没说出来,就会没完没了地重复当时最时髦的话“They tried to identify themselves. “ 这句时髦话谁不会说?还有那位后来出现在翡翠台的外国人的的空洞发言也占了不少时间。所以后来我声明从此后拒绝 BBC 的任何采访。
那些外国人还要争,在国外是谁第一个发现《黄土地》的。公认的是PAUL CLARK在香
港电影节上发现了《黄土地》,然后把它弄到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上去的。( 很谦虚地说 ) 据我所知,在此一年以前,伦敦的一家电影院已经正式公映了这部影片。香港电影节是《黄土地》第三次在国外露面(第一次是我前面提到的幻灯片)。第二次是在这事情是伦敦的那家电影院,这是英国电影评论家TONY RYAN 帮忙安排的。我保存有该影院公映《黄土地》时的海报。是那位影院经理寄来给我的。这段事大概只有少数几个有关的人知道。
后来,虽然第五代已经名存实亡,但是从他们现在的作品中依然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开放空间的处理。第五代的作品再“臭”(后来者语),无论如何也不能抹杀第五代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对中国电影语言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只能遗憾地说,他们失去了(或者说被剥夺了)继续做下去的机会。可是台湾的杨德昌和侯孝贤却做下去了。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存在的东西我不会说不存在。我在下一章将要谈到他们在空间上的突破。 我对第五代没有任何责难,因为我深深了解他们的处境。奉劝某些人,看看你们自写 的文章,为什么那么写,那么片面?难道你们就不能拿出对待第五代的精神来对待自己 的臭文章吗?你们可能会有充分的理由来解释你们写文章时遇到的困难?难道他们就没有?这种人就是想获得什么成就 on someothers expense, 非常卑鄙可耻。想要成为一名和学术有关的工作者,第一个要求就是诚实,但我指的不是那类一面贪赃枉法一面宣称自己是个襟怀坦荡的人的那种卑鄙的诚实,可千万别学他们,他们是腐烂的。这里我谈到了一些事情是过去我从来没有提过的。我认为没有必要提,而且不愿多惹麻烦。即使有时觉得应该提一笔这些事实的时候,总有年轻人好心地劝我,这样做人家会认为你是在吹嘘自己,是你想沾第五代的光。我有过这样的经验。在九十年代,深圳有人办一个班,要我去主讲。可深圳骗子很多,报名来学的人都要打听主讲人是什么人物。所以主持人要我事先介绍自己,我就拿出一些记录镜头给他们了。这时又有人说了,是不是过分宣传自己了。可我心想,我还没全拿出来呢。现在我已经是一个行将就墓的老人了,已经无所作为了,也什么都不在乎了,谈谈一些没人提的,过去的事实,总不至于还有人怀疑我有什么别的企图了吧。
十五、MTV 的空间-先锋派的观念从形式上进入商业电影
MTV 是1981年在美国出现的一个电视台。 我们总是捡洋落,连MTV 是什么都不知
道,又来个什么“中国特色的MTV ”,真是“真正中国的可口可乐” 。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总是喜欢干一些丢人显眼的事。我最初听到说,中国的电视
台也搞MTV ,吓了我一大跳,一个不断在呐喊“先锋派的乌云出现在中国电影的地平线上”,“先锋派的乌云笼罩着中国电影”,怎么一下子也搞开先锋派的东西了?跟西方的共产主义讲和了?是不是一个大误会?原来中国有一句俗话,叫无知之勇。比如说,在做大报告的时候,把西方的“经典作品”(?) 斯特劳斯的圆舞曲和我们的经典作品高山流水相提并论。
我们先来研究一个好莱坞商业电影的情况。
1979年好莱坞摄制了一部音乐片叫《ALL THAT JAZZ》,这部影片成功的把先锋派的手法和商业片的传统成规结合在一 ,获得了成功。观众接受了。这部影片里的空间处理是跳跃的。比如说,一个跃起的舞蹈动作,在那个舞蹈演员脚还没有着地以前,或者说,当这条运动的曲线刚达到顶峰时,镜头就切至另一个舞蹈动作。按传统的概念,那个演员岂不是悬在空中了吗?或者是一组舞蹈演员在跳一段动作,接下来非常流畅地接到另一组舞蹈演员在跳同一段动作,然后又换。这样又变成了非常随便的时空转换。或者是在同一个位置上不断有许多演员连续出现完成一个动作(比如说,旋转的动作)。这都是时空上的突破。时空完全摆脱 了叙事逻辑的束缚。
所以MONACO 可以在他的那部《怎样读解一部影片》的修改版里增添的一段“八十年代 及其后”中提出,商业电影与先锋派之间的界线已经没有了。这还是一个观众的问题。
MTV 是广告,为推销唱片、歌星而制作的广告,而且是一个可供直接消费的广告,也就是 说,这条广告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观赏的节目。有人说它是后现代的产品。它打破了叙事的成 规,也就是说,它不叙事,它的镜头变换不按叙事逻辑。它的时空变换是随意的。
(它们非常推崇二十年代的德国表现主义。我们从麦唐娜早期的 MTV 中可以看到LANG 的 《大都会》(METROPOLIS) 的地下工厂的布景。这堂布景以变奏的形式出现在不少 MTV 的作品中。(而我们的所谓中国特色的MTV 时空是三十年代最落后的时空,其制作水平 [如节奏 ] 还不如三十年代的好莱坞的音乐片。)我们声称,我们不搞“视觉轰炸”,那么搞什么呢?噢,原来在搞文字轰炸,没有视听节奏,只是一句歌词剪一刀。为什么不诚实地说,我们不会搞视觉轰炸,所以只好在视听媒介中大搞文字轰炸。你叫他唱歌,他要革新,只朗诵,不唱;你叫他朗诵,他要革新,只跳,不朗诵,你叫他跳舞,他要革新,只唱,不跳,你叫你叫他唱歌,他要革新,只朗诵,不唱;你........真是江青的徒子徒孙。在这里我要告诫那几位发明如此惊人倒退的电影形式的先生们,中国人有十几亿,你们那一小撮不仅代表不了十几亿中国人,而且没有资格代表,不要什么东西搞不好,就拿中国人来 垫背。无耻!哪里学来的臭毛病! 谁给你们权利来如此糟蹋中国人的? 看到具有“某些人的特色”的MTV 的惨状,我下决心办两个MTV 的班,第一个班的成绩还可以,可是多数并不是想制作MTV的,第二次只来了报名者,我还是讲了。第三次在天津,课上对我对学员说,不要一句歌词剪一刀,要跟着音乐剪。一位学员提问,怎样按音乐剪? !!!!!我决心不办这种班了。这叫对牛弹琴。连音乐都不懂就敢拍MTV,不过那不懂音乐的人,连MTV 都只是头一会听说的老头不也当上了在中国MTV 的评委了吗?这确实是目前大陆中国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