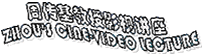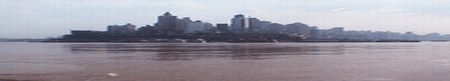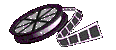十、 光学透镜的焦距形成的空间
我们读物理的光学时,书里都讲到过光学透镜和光学透镜的焦距问题。不同的焦距所造成的影像是不一样的。从电影的角度来说,我们考虑的是通过光学透镜,实际的被摄体与银幕上所形成的影像的空间透视关系问题。这不同于只用一个接近于人眼的焦距,如50mm 或70mm 的光学透镜来拍摄各种不同距离的被摄体在银幕上所得出的空间透视效果。
一般来说,我们把各种不同的焦距分为 28mm 的广角镜头, 50mm 的普通镜头和135mm 的望远镜头。广角镜头把空间的视野宽,纵深空间变长了。因此不仅被摄体与摄影机位的关系变长了,而且镜头内的空间关系也变长了,线条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形,纵深感强。普通镜头最接近人眼的焦距。望远镜头的效果就和望远镜一样,把空间的纵深压缩了,因此远处的被摄体显得移到了前景,镜头内的空间显得全都压缩在前景,线条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形,扁平感很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焦距的光学透镜不仅有视角的不同,而且还有纵深透视效果的不同。所以摄影机的运动所造成的空间透视的变化和改变焦距(变焦)所造成的空间透视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从广角变为望远的过程给观众的感觉是照片的逐渐放大,而不是物理距离的变?br> 六七十年代新型的变焦镜头出现后,在电影制作中出现了滥用变焦镜头的现象,这是每次新技术出现时带来的必然后果。别忘了,当录音技术刚出现时,那时的影片在片头上一定注明是:100%TALKIE (百分之百的对白片,多可怕!)。和瑞典电影大师伯格曼长期合作的摄影师奈克维斯特就曾说过,新型的变焦镜头出现后,简直是一种诱惑,只要手指一按钮,空间关系就变了。在六十年代出现了滥用变焦镜头的现象。后来大家终于明白了变焦的效果与摄影机运动的效果完全不同。在七十年代末在美国出现了几篇讨论变焦的论文。有人提出,变焦最有效的用法是作为一种哲理性的运用。比如在美国导演阿尔特曼的影片《麦卡布和米勒夫人》的结尾处,一个用广角拍的美丽的雪景,但变焦推上去,在远处森林的边缘有一个人被杀了。也有外国的电影创作者到北京来,看了一些我们的国产片,就提意见说,是不是把变焦镜头扔到窗外去。
变焦镜头使用得当是很有力的表现手段。希区柯克在《晕眩》(1958)一片把两种不同的空间透视关系的变化结合起来使用造成了十分特殊的视觉效果。具体地说,他把变焦与移动镜头结合起来从上往下拍摄一个楼梯井的镜头,成功地造成了主人公恐高症的晕眩的心理感觉。他的做法是把楼梯井的模型侧放,摄影机对准楼梯井口,处于远处慢慢推向模型,而变焦镜头开始时处于长焦(望远镜头)慢慢拉成广角,要求是模型的大小
在银幕上必须保持不变。这个持续仅几秒钟的镜头花去了$19,000。
希区柯克给我们的启发是,把摄影机与被摄体的距离近、中、远和焦距的变化广角、普通、望远结合起来使用,三的三次乘方,至少有九种基本的空间关系的变化。
在这之后,连一般的影片都这会这样的使用来达到某种特殊的效果。我看过一部1989年的日本娱乐片,片名我叫不上来。其中有一个段落是影片的女主人公做了一个梦,她抱着许多书走出办公室,转身就撞到一个男子,她抬头一看好象是不认识,对方也好象是不认识她。可是我们观众全认出来那男子就是她生活中的男朋友。做梦嘛!那个男子跟她打听一个科室,她就告诉他怎样走。之后那男子就离开,沿着过道朝纵深走去,她回头看了一阵,然后抱着书继续朝摄影机走来。这一段的镜头处理是,从普通镜头慢慢变成广角(显得那男子越来越快地离开她),同时摄影机随着女主人公向后拉(表示女主人公也朝反方向离开了),但始终保持人物大小不变。这种镜头效果似乎造成了一种莫明其妙的感觉:明明是她的男朋友,可是在梦里又不认识。
在国外的纪录片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处理,比如在运动的汽车上拍摄迎面驶来的一辆车,同时变焦拉成广角,从面造成一种似动非动的效果。
可是在中国,不仅在实践中把变焦当移动镜头使用,而且在那部《电影艺术辞典》中的变焦词条中说,变焦可以代替推拉。我感到奇怪地是,为什么这个词条不请刘国典老师来撰写,而要找一个不懂光学透镜的评论家来写。更严重的是,这个词条在多少年前就在某电影杂志上出现过,我当时就给该杂志的主编指出这个错误,并且请他们向刘国典老师请教一下。结果是不予理睬。这就是中国电影的实情。这种把变焦和移动镜头等同
起来的做法,就是把九种不同的变化变成了三种变化。这岂不是自己堵自己的路子吗?
大概是嫌表现手段太多了。
作业:用傻瓜照相机拍九张不同空间关系的照片。
要求:被摄体是三个人各占据近、中、远三个位置,近景的人处于画面右侧,中景的人处于画面左侧,远景的人处于画面正中。三个人始终站在自己的固定位置上不动。
第一组的三张照片用同一个固定机位。 第二组的三张照片用同一种焦距。
第一组(同一个固定机位)
第一张照片:用广角镜头拍。(条件如不够,用小于50MM的焦距即可)
第二张照片:用普通镜头拍。(50或75MM)
第三张照片:用望远镜头拍。(大于75MM的焦距即可)
第二组(三张照片都用同一种焦距,自己选择,或用广角,或望远,或 普通)
第一张照片:(用第一组的那个固定机位) 第二张照片:机位向被摄体前移一米。
第三张照片:机位再向前移一米。 第三组(前景的那个人的大小不得变)
第一张照片:用广角拍,机位的距离自己找,以前景人物大小不变为准。)
第二张照片:用普通镜头拍,机位距离自己找,要求同上。
第三张照片:用望远镜头拍,机位距离自己找,要求同上。
仔细观察这九张照片中,那三个人之间的空间关系不什么不同的变化。
十一、日本电影的空间观念
日本的电影现象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日本和我们一样是一个东方民族,电影不是我们发明的。根据记载,卢米埃尔兄弟的代表于1896年同时到了上海和东京。可是现在日本却有一个全世界都承认的日本民族电影风格。而中国还在“你说我说”呢。正如一百多年前日本用自己造的军舰和大炮打败了中国购卖的洋枪洋舰。这个传统似乎继续到今天。人家也没有大喊大叫地要弘扬什么,但是却弘扬了。有能耐的人只干不喊的。放心
好了,大喊大叫的人都是一事无成的,最叫人看不起了。
世界公认的日本民族电影大师有两位:小津安二郎和沟口健二。他们都是从默片时代就开始拍电影的。小津是从学习好莱坞电影儿开始牟,而沟口是从学习欧洲电影开始的。1930年小津拍了一部名叫《东京大合唱》的故事片(我始终没有机会看到这部影片)。根据看过此片的外国电影史学家和理论家称,他的影片够好莱坞水平。可是1931年小津的影片中的电影语言似乎是完全和好莱坞对着干的。最明显地表现在,小津根本不遵守好莱坞电影儿所立的那个轴线的成规。在他的影片中可以出现这样的镜头关系。第一个镜头父亲把球从右往左扔出画外,在第二个镜头里,那球却是从左往右飞入画内,儿子接球。
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他的剪辑师忍不住跟他说,你错了。小津问他怎么错了。剪辑师就指出他越轴线的问题。小津说,那你来拍一个正确的。拍好后,把两个方案一起放来看。小津看完后说,没有什么差别,都可以。
1955年黑泽明的《罗生门》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后,日本电影引起了全世界电影界的瞩目。我这里说的瞩目是真的瞩目,而不是那种知吹自擂的所谓瞩目。美国的电影理论家波德维尔说( BODWELL)), 日本民族电影的风格使美国人认识到,好莱坞电影的拍法只不过是电影语言的一种风格,还有其它风格,比如说,日本电影。而到了八十年代,十分明显地是,好莱坞电影儿在学日本民族电影的语言了。比如说,《给戴维小姐开车》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以上所说的仅是事实。那么小津这样做有什么根据,还是仅仅为了反而反。我曾做了一些调查,最后是日本电影理论家佐藤忠男给我的解释最合理,而且最有参考价值。
佐藤忠男说,从日本电影的银幕上就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主要是二战以前)日本封建社会里,人们跪坐在铺在地板上的塔塔米上时,两个人是面朝一个方向跪坐的。日本的规矩是直接看着对方的面孔是不礼貌的,尤其是男女之间更不能如此。所以在生活中,日本人就没有那条面对面的所形成的兴趣线(即轴线),他们怎么会有不能越过轴线的概念呢?这才是电影语言的创造性的创新。小津不是把其它艺术的成规搬进了电影,而是把日本民族的生活习俗纳入了镜头之中。佐藤忠男告诉我说,日本电影所遵循的不是180 度的轴线概念,而是 360 度的空间概念。我在《罗生门》一片的读解中所分析的那六个镜头的段落,恰恰是正反两个360 度。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曾向《没有下完的一盘棋》的日本剪辑师请教过。他没有讲什么理论根据,只是说,这是一个感觉问题。感觉对头就行。确实如此。在一次全国剪辑会议上,我提出日本电影的这个特点,但是有许多剪辑师(按理对此应当十分敏感)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因为感觉对头就行,所以看到越轴的现象却没有感到蹩扭,也就放过了。另外还有一次在上海开会,和上影厂的一些导演一起看《给戴维小姐
开车》。散场后,
我问那些导演,越轴了吧!他们说,什么?然后回想一下,可不是吗?我们知道,上影的老导演们很讲究这根轴线,可是人家越轴了,也没有看出来。七十年代的《巴顿》至少有四处是越轴的。
不过我们不说日本民族电影风格是可以越轴的。人家没有轴线的观念,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观念强加于人。
而沟口健二本人习画,他受欧洲长镜头的影响最深。但他并不是抄袭欧洲的风格,而是把日本歌舞伎的空间观念和日本绘画的绢轴画的空间观念结合起来,形成了很独特的风格。比如说,他的摄影机在院子里横移,经过一个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都有事件,就象绢轴画那样慢慢地展开。他在景别的运用上也十分独特,在他的影片里没有特写。他认为特写没有表现力。当他的人物向摄影机走来时,他的摄影机就往后退,总是不让他走
到近景的距离。他认为远景是情绪感染力最强的。其实他他强调的是环境的感染力。这可能是东方的特色。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你看这景别不是越来越远,而在情绪高潮时,那主人公只不过是天边的一个小芝麻粒。法国新浪潮对长镜头和环境有特殊的兴趣,当他们了解到沟口的影片时,他们感震惊。因为沟口在二十多年前就实现了他们的想法。他们把沟口崇拜为英雄。关于环境与人的空间关系,(详见十三、电影空间变化的发展进程。)
其实这是十分超前的观念,人和环境是不可分离的。如何发挥环境的情绪作用,对于那丞只会用特写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新课题。另外,他的时空转换也是十分独特的。他经常是在一个镜头中转换时空。我有些不太愿意讲沟口的时空转换,因为要让北京电影学院的那位专讲三个时空的教授知道了,又不知道会把它庸俗化到什么程度了。在故事片中在一个镜头中转换时空是比较容易的,可以做手脚。比如法国新浪潮的影片《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中,女主人公从房间的一角(显然是夜景,窗外是黑的,屋内是点了灯的。当女主人公走到房间的另外一角时,窗外是白天。这很容易做到。沟口的影片就经常这样来变换。在有一部影片中,那个孩子从药店走回家,当他走到一个拐角处,他拐了,可是摄影机没有拐,一直往对着对面的墙推到很近才停下,过了一阵,摄影向刚才那个孩子拐弯的方向摇过去,可那是另一处的街景。可是在《雨夜物语》中,沟口却没有做任何手脚。那个烧冥的人在市镇上中了邪,和一个女鬼住了一个时期,后来一个和尚救了他。他清醒过来后就赶回家去。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已经死了。他进屋就喊“宫本,宫本”。可是没有人应,屋里十分荒凉,他也没有理会,只顾找他的宫本。他一直跑到后院,又从外面(我们透过屋内的两扇窗户看到他的运动)绕回到屋里,进屋后看到他的妻子(在前景在灶前烧饭。这是由一个镜头完成的。第一次看确实把观众震住了。当然,一个专业人员看第二遍时就明白,原来是当丈夫往后院走的时候,摄影机不但跟摇,而且同时往后拉,但是因为摇的方向和后拉的方向是一致的,不容易觉察。
题外话,我把这一段放映给这么多的学生看,几万人吧,没有一个在第一、二次看出它的窍门的。只有一位学生声称他第一次就看出摄影机同时在摇和后拉。这确实了不起。但是后来我有意不做任何暗示地放给大家看,然后请这位学生来分析。他分析得一塌糊涂。抱这种态度是什么也学不到的,自己骗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