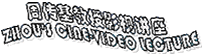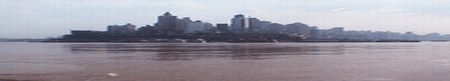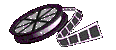四、中国不同时代的社会的人物关系的空间表现
那么我们来研究一下,中国的人物关系从空间表现上来说是怎样的呢?你们知道抗战前中国社会的男女的空间关系是怎样的吗?不知道?那你怎样评论一部关于抗战前中国社会的故事的影片,其中有男有女?那可真叫瞎评。抗战前的中国社会是那样的吗?能从那里找出心啊,灵魂啊?1937 年以前我还小,刚念五年级。可是后来我的一位老师告诉我,那时他在某女子中学当教务主任。女学生如果犯了错误要叫到他办公室来谈话,他必须先把一张椅子摆成和他的办公桌成90度角,椅背冲着他。女学生,报告!进来!她一进来就屁股坐在那张为她专门准备的椅子上,于是就变成了她背对着教务主任坐。教务主任的指着她的背脊梁批评她,你怎么样,怎么样。多棒的视觉画面!可是四人帮抓起来以后的时期,曾出现了三部关于抗战前中国的女学堂的故事,有男老师和女学生。他们的空间关系可是开通极了。多可惜。别说我的老师的经验了。就是我念高中的时候,那是1941年以后,尽管是在教会学校里(一般认为比较开通)还是男女授受不亲呢。男生和女生说话,若被老师看见要记大过的。可笑的是,大家都知道高中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状态,男女生不许说话,男生就欺侮女生,这不记过。表示亲善要记过。我有过一次经历。当时学校在四川成都的乡下,一次我周末回成都燕京大学表姑家,她的一位同事的女儿和我同校,因为她那次没有回家,所以她母亲就要我把一个包带她。长辈的话能不从吗?可是老天爷啊,我怎么交给她。心里倒是想交给她,因为她是我校校花,刘诗琨的妹妹。回到学校,晚点名,全校学生集中在寨子的大院里,男生站一头,女生站一头,大眼瞪小眼。男生们大都悄悄地在说,你喜欢哪个,你喜欢哪个,那个?不行,我喜欢哪个...... 女生如何不得而知,因为没有到那边去过。我手里捧着那个包,越来越沉。再不过去,晚点名后就找不到她了,那她母亲那里如何交待。说我贪污了。终于鼓起勇气,硬着头皮,跨过那分界线的 NOMANSLAND。只见对面全体女生用视觉语言盯着我“你好大的胆,你过来干什么!”同时背脊梁刺痛。那些男生都在盯着我。好不容易强渡到彼岸,可她又不站在第一排,我得穿过那严阵以待的若干层女生,到达她那里,连头也不敢抬,把包往她手里一塞,说了一声,“你妈给你的”。回过头来就准备往回跑。可是我被钉在了那里。对面全体男生都用愤怒的目光盯着我“好大的狗胆,居然敢在大庭广众前过分界线,而且找的还是校花!”我至今回想不起我是怎样回到那一边的。如此紧张的关系,怎么在我们的影视作品中是那么的轻松?
当然,现在时代不同了,男女的空间关系也变了,更进步了。你们可以在公共汽车上搂着对方的脖子!我觉得搂着腰已经是了不起了,这是公共场合嘛。把脖子搂得紧紧的,也不怕车上的人看。到了公园里,那更是有得看了。那长条椅上坐着两个谈恋爱的男女,两个脑袋,四条腿,我总分不清哪两条腿是属于哪个脑袋的,全缠一块儿了。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空间关系总得研究透吧,人家看我是个老流氓,怎么总是盯着人家谈恋爱的。我觉得我够开通的了,不过这...... 你们看,我只不过在这里讲了三个时代的中学校的空间关系特点。这要摆进电影里,那语言是多么地丰富多彩啊。只会“你说我说”“你说我说”“你说我说”“你说我说”“你说我说”,这样做是不是不懂电影。我没有说过分吧。不过我们网上有的年轻人说,拍电影的人不一定要懂电影。他大概又是在为自己拍电影铺路吧。找个人妖来,还能证明世界上没有男女之分呢。这也没有什么高明的。
还有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我们叫保护空间,即一般不容他人侵入的空间。有人的这个空间大些,有人小些。一般来说,全世界的女性的这个空间要比男的大。有人对此没有感觉,总喜欢往前凑,真叫人讨厌。为了礼貌起见,你也只好往后退,让开他,可他还步步近逼。我就遇见过这样的人,两人一路走,他总是侧过身来跟我说话,他的头都接触到我的肩膀了,多讨厌。我往右挪一一步,他往右来一步,最后把我逼到墙根。还不好意思,要给他留面子,于是蹲下来,装着记鞋带,然后乘机转移到他的左边来,于是他把头侧向我的右肩,我只好往左挪一步,他跟一步。最后郑洞天老师在后面嚷嚷说,你们两个在干什么,不断走之字形。这也是一种性格吧,或者.... 我在飞机和火车上总要跟旁边的那位发生磨擦。在我思想里,每个人都买了票买了一个空间,你为什么要到我的空间范围里来。你看,在硬卧车厢里,对面那位先生还没有等车开,就把鞋脱了,一双臭脚丫子伸过来,搁在你的座位上,摆到你鼻子底下。当你请他把脚挪开时,戏就开始了。在飞机上,有人非要把他的胳膊肘的三角形越过手扶把摆在我的胸前。这一路我就整天守着他那三角形?当你请他把那三角形收回时,他于是操着上海腔说,“啊呀呀,你这个同志怎么搞的”。我怎么搞的?得啦,戏又开始了。
你再读一下公共关系学吧?你去求职,见了经理应保持什么样的空间距离合适?工作谈成了之后可以把空间关系调整到什么程度?这都是生活里的经验。可我们的“你说我说”“你说我说”,甚至连哪个是站着的,哪个是坐着的,观众都没有分清楚,直到一个人最后站起来了,观众才明白,原来他是坐着的,人物关系的视觉距离也没有了。一切只靠对话,搞舞台剧去吧!那里缺人。
这都是我个人的生活经验,你们有你们不同的生活经验。大家凑凑,可多了。多到都轮不上用“你说我说”“你说我说”。我现在还没有谈纵深空间呢。
五、电影本体的空间问题必需多多练功,有困难,自己想办法解决
当你遇到一件你从来不知道的事情时,你抱什么态度。这个问题你们在中等教育中没有接受过。你们在中等教育中学到的是,当你遇到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那一定是坏的,因为对的,正确的,老师都讲过了。所以对新的东西只有批。 在讨论中有人指出,我在本体论、综合艺术论和心理学方面都是无知的,因此估计大概我讲的本体也不会多。
请大家一直记住上面这些话,作为判断我的教学的标准,以免上当受骗。这就是INTERNET的优势,畅所欲言,因此也可以做到自动大暴露。 尽管是畅所欲言,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我对电影的本体研究了几十年了,才下的结论,可说这话的人听见别人说电影本体这个概念还没几天,居然敢轻下结论。自己什么都还没有
弄懂,却敢轻下结论。甚至当我正在讲本体时,有人都会理直气壮地质问,你为什么不讲本体?记得八十年代中在北大的一次讲课。我讲了不到二十钟就递上一张条子来,上面写道:请你讲电影艺术。我的回答是,“我正在讲电影艺术。” 我们的中等教育真可怕。调查.研究?我们外国电影研究室24个人做了十几年的资料(英,法,德,日,俄,意,波等文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被人踩在脚底下,是具体地踩,剪报上全是各种各样的鞋底印,全部被毁。我所在的单位也成了被砸烂的单位。他们的敌人做不到的,他们自己不仅做到了,而且非常彻底。有人对此抱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这是因为他们的时间精力本来就没有什么价值。可我的时间和精力是有价值的。这样来对待我的劳动成果,是犯罪行为。这种被确认为合法的破坏行为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可以信口胡说,不需要任何根据,不需要查找资料。虽然这是中国大陆社会盛行的特色,但我仍不希望
你们成为这样的人。这种思维方法最终是对自己不好。 我从不相信皇帝的新衣的。
你们可以注意,看看我讲的本体是不是讲到这个讲座结束还没有讲完。
电影本体带来的另一方面的课题就是人的眼睛是怎样看的,这是心理学的课题,至今它们还没有得到非常科学的结论。由此可见,电影语言是随着心理学前进的。有人迫不及待地反本体,这么急迫干什么?他们反对的态度就好比是一个人看到那垒球投手准备投球,刚刚做出把手伸向后面的动作时,马上就非常聪明地朝那垒球投手喊去:“喂,你的对手在正前方,不在后面!”也难怪,因为他从来没有玩过垒球。可是这人又会反驳我说,“没有宰过猪,还没有吃过猪肉!”在没有实例给大家看的情况下,你爱怎么说都行。等到技术问题解决了,心理补偿和心理认同,以及车轮效应等等都可以用实例来说明的时候,可别忘了你们现在说的这些缪论。
我再强调一遍,这几个问题没有实例根本没法谈。而这几个问题没有体出来解决,那就根本没法讲剪辑。别忘了,我们讲的是电影。黑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你们自己设计的五个镜头的作业已经看了。我再强调一次,有一种作业的目的是讲究“对与错”。我认为这种方法作用不大。有一种是只要你动了脑筋做了作业,那就会有收获。不是对与错的问题,也不是什么“太简单了”或“太复杂了”的问题。我的教学方法和你们所接
受的中等教育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澳大利亚电影学院AFTRS 有一条经验。只要上过剪辑台,那个学编剧的学生写出来的剧本就跟他入学时交的那个剧本完全不一样。第一个剧本不是象小说,就是象话剧。第二个就更接近电影了。搞电影评论的学生也一样。我的教学方法都是参照这些成功的经验的。我的教学方法是要学生学会动脑筋,最终要求他们超前人。而不是学会唬,咋。
你们不妨花一点儿时间研究一下,在我们国内那怕是高级编剧班培训出来的人写的剧本,从他的行文里就能看出来,是不是只能拍成“你说我说”?一位香港的电影制片人,(他没有学过拍电影,是做生意的)看了这种剧本后说,没有运动,那叫什么电影剧本?你看,在正常的环境( 没有泛滥成灾的综合艺术论的干扰 ) 中做电影生意的人很自然地就懂得电影的本体是什么。我们的编剧恐怕连他自己写的那一段落的地平线在脑子里都看不见,所以也画不出来。另外再研究一下报刊上的电影评论,你把文章中的“电影”或“影片”都改成“文学”或“小说”,你看文章是否依然成立?那是文学评论。文笔再好,也只不过是文学评论:用普通观众的眼睛看完了电影,用高中语文课的作品分析的方法写出一篇文章来,用词藻取代了影片的实质,这就算影评了。我想各位现在也可能已经感觉到,我们现在离那抽象、概括和带随意性的符号系统越来越远了。慢慢地你们就不用到文字中去找感觉了。可是我们还没有涉及到声音呢。?br> 要知道,我的考试一般都是考卷上写一个字扣一分。别看我在国外的讲课只给一两个学分,在考卷上写字一样扣分,不会画的人照样不极格。有的学生又是未经我的暗示,就捧起我来,说这是电影学院唯一的电影的考试。我受之无愧。
MUSE的理解最准确,就是当镜头顺序改变后,最理想的就是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故事。大家可以再想想看,你的作业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吗?有一条经验要告诉你们的,剪辑是整个影视作品的最后完成阶段(包括声画合成)。精剪是一门大学问。在我们中国的电影制作中,对此缺乏认识,因此后期制作的时间很短。在国外,甚至一部纪录片也要花上两个月的时间来剪辑。(请不要跟我说什么钱少的问题,我是圈内人,对于这种人我的回答是现成的:少一点假公济私,少浪费一点,少私分一些,先别急着给自己买汽车,钱会够的。或者说,贪污浪费者一律吃官司,钱准够。可是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更大的多的贪污“犯”还多着呢)
我要求同学把自己的一个作业修改了再修改,半年或一年以后你再回头看你第一个方案。你会感到非常吃惊的。不过做不做是自己的事。
从中央台的节目中就可以看出,创作者丢东西。也就是说,我明明看见播出节目中的镜头里有很多东西没有利用。有时不需要看那个节目的原素材,仅从它的完成作品中就可以看出镜头顺序不合适,大有修改的余地。他们经常把重点摆在解说词上,可是有时只消把两个镜头的顺序前后一调,解说词就可以完全不要了。有时我在家里用两台民用录象机就可以改过来了。大陆中国的影视作品中特别喜欢用特写,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这一段缺一个黄色块,正好有一个镜头里那被摄体围着一条黄围巾。可偏偏拍的是远景。如果是特写,那么这一段的色彩节奏就形成了。或者是前景上的人物在运动时,后面露出了一个穿黄衣服的人,可是一剪刀,就剪掉了,然后用解说词的中看不见的“五彩缤纷”来取代之。
既然电影语言是模拟人的视听感知经验,那么就到生活里去找素材。别上其它艺术中去找下脚料。雕塑在生活中寻找素材时,只找动态的瞬间。电影找的是运动的过程。修行在自己,就是一个“练”的功夫。这跟学习钢琴是一样的。弹钢琴不靠嘴皮子,靠手指头。会拉小提琴吗,不会,那你怎么知道小提琴的STACCATO 将来会变臭的,而不是自己说的这句话是臭的呢?STACCATO 是小提琴演奏系统中的一部分,是左右手的配合关系问题,只不过它的要求到极限罢了。STACCATO不会单独臭的,除非整个系统都臭了。那么小提琴也可以烧掉了。谁教出来的,真够愚昧的。这叫无知之勇。这种人在大陆也太多了一些。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再到影视杂谈上去把旧的贴文翻出来看看,你们对自己不认识的东西都说了些什么?谁教你们这样来对待事物的?这叫中国学生的知识比外国的学生丰富,所以能提出各种古怪愚昧的问题来?可说这话的人却到那知识浅薄的外国去念博士后,真够愚昧的了。别忘了,你的导师也是从那些你认为是傻子的学生变过来的。我不希望到我的讲座来跟我学的年轻人是这样的。
另外,学琴的人每个星期只上老师那里去一个小时,我们叫回琴。可是一个星期你至少要在钢琴上练三四十个小时(不是练嘴)。你的进度不由老师掌握,而是由你练琴的程度来掌握。有些家长经常会问老师,我的孩子要学几年。老师的回答一定是,这决定于你的孩子,练得多进度就快,练得少进度就慢,甚至一辈子也学不成。
中国穷,学电影,工具不齐全。这方面我做过长时期的考虑,这个问题不解决,电影的学习就没法进行。象北京电影学院那样,虽然某些专业的学生可以享受到使用制作设备的权利,但是下午四点必须交机器,因为工作人员要下班了,(可就是不设三班倒),学生就没有办法在黄金时间拍镜头,更没有办法拍夜景。看来,招学生是为工作人员谋识用,是学生为工作人员服务。我私人办的班最后终于能做到把机器长时期交到学生手里保管,让他们把什么时间的光都拍了。在没有配套的设备以前,目前至少大家都有一台录象机。可以合作,两个人把两台录象机和起来用。记得LANCELOST曾说过,他用电脑上的那个PROGRAM 随便玩,很有意思。要知道,开头是随便玩。就跟早期的电影先驱者那样,偶然地机器出了故障。修好了接着再拍。还放时就变成了大街上行驶的一辆马车突然消失了。于是就找到了停机拍摄的手法。到了二十年代欧洲的先锋派,也就是在中国大陆被恨之入骨,几乎要把它打成反革命的那个先锋派,就已经是有意识地在探索电影的表现可能性。香港有一个说法,先锋派人人骂,先锋派的手法人人用。先锋派的实验给我很大启发。尤其是有了电子的录象手段后,根本不需要在制片厂里被领导看中了允许当导演了,才有机会玩电影。我在家里就玩,谁也管不着。有一段时期我就是漫无目的地录电视节目,边录边换台。有一次还放时,京剧的一个踢腿,接足球赛的一只飞出去的球。看起来就是那个京剧人物一脚把球踢了出去。其实这就是视觉上的镜头与镜头之间的相对时空关系。这也就是说,把你手中有的一些录象带看它几十遍,然后把某个镜头按你自己的想法与另一个镜头相接。这个做法包括了好几种训练。
读解素材的能力越来越强,各种视觉关系掌握得更多。视觉记忆力越练越强。你甚至能编出自己的故事来,这也就是视听思维的训练。当然会有很多局限,但是这种局限又使你认识到,如果有条件的话,你还能做什么。
这里顺便提一下学习方法的问题。
我学电影完全是自己想办法,虽然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员,还是要自己花老本来学电影,电影学院从来没有给我提供过任何学习的方便,每个学期都有课,从来没有轮换的机会,更没有给过什么教学或教研经费了。不过,我倒是领过几十个插盒录音带,第二年再去领的时候,那位正式获得“红管家”称号的管钱的人跟我说,你去年不是已经领了几十盘吗?用完了?消了再录嘛!我只回了他一句话,你是一个黑管家。有一个学期因为电影学院买的那些廉价的设备(我对此到现在还是打一个大?)达不到预期的讲课效果,我还得每次上课都带自己的录象机去。我自己花钱做出来的六十小时的实例,在学院用,从来不给资料费,但是如果要用学院的资料,那还得另外付给学院资料费,系里付不起,只好不用。最后还落个怀疑我偷了学院的资料。帮忙出力的只有学生。这种教学条件真够可以的。但是几十年来我已经习惯了。这难不到我,我还是学成了。象我们这一代人,从来没有奢望过会得到什么良好的客观条件。全靠自己干出来的,可是还不断要我们表示感恩。可是只靠自己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好处就是,你不需要对任何人感恩戴德!也没有皇恩浩荡这一说!事实证明,只要想学,任何困难都难不倒。办法靠自己想。我不仅用这种方法弄懂了电影是什么,而且在采用一些案例时,由于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我用两台民用录象机就做了修改。我用民用录象机剪出几个不同的方案(一般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来让学生做判断。我还剪出了拍子准确的节奏段落。后来我有了摄象机,那就更方便了。我和那部现代罗米欧的影片的录音师DAVIS 交换过意见,我们都认为,在学习的过程中,设备差, 练人,设备好,养懒汉。讲到那里,作业就应做到那里。自己想出题目来。不要等老师提出来还不太想做。
另外,根据目前的条件大概每个人都能弄到或借到一台傻瓜照相机,在没有摄象机的条件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静态的照相机来代替。就是用拍电影的动态思维来拍呆照。经常有人说我拍的照片不知是什么东西。他们不知道那只是一个镜头中的一个画格。开始时只准用黑白胶卷。
|